
歐洲飛回北京的航班上,戴威做了一個艱難的決定,“封校”。
時間是2016年初春。手握1000萬人民幣A輪融資的ofo大舉擴張,校園數量從5個激增到25個,日訂單量卻卡在兩萬單,不增反降。戴威意識到,學校規模增加了,單車數量增加了,但是密度和使用頻率下降了。
當時還關在校園運營的ofo,被騎出校門無法收回,一時間變成“海淀小黃車”。投資人的電話打過來,“城市用戶沒有學生證不能注冊認證,在街上看到小黃車不能用,提前投放城市吧。”戴威并未采納這一建議,而是把車堵在校園。
坐在位于北四環的理想國際大廈11層ofo北京辦公室,回憶起當時的困境,ofo創始人兼CEO戴威依然面露苦色。對于他來說,那是一個不完美卻不得不做的決定。
戴威調派運營師傅滿城去拉小黃車回校園,但是,“架不住學生騎的多。”ofo聯合創始人楊品杰說。創始團隊五個人討論了兩個晚上,最終決定封校,“當時在武漢是全封,北京、上海實行單雙號限行。單號車只能在校內騎,雙號車交99元押金可以騎到校外,但是必須本人騎回來。”到了5月份,訂單一下子起來了。
如果時光倒流,戴威或許會采納投資人的建議。在ofo聯合創始人薛鼎看來,“如果那個時間點開了城市,或許摩拜就沒有機會了。但是一旦車丟了,沒有投資跟進了怎么辦?只能說風險越大,收益越大。”
上線第一天,走在北大校園,身邊一輛輛ofo經過,ofo聯合創始人薛鼎感到興奮,“當時連APP都沒有,只有微信服務號”
結局終究無法假設,ofo雖未在一年前掃清戰場,但是在過去一年半,交出了一份漂亮的成績單:開拓城市近40個,連接單車超過100萬輛,注冊用戶超過1500萬,為用戶提供出行超過2.5億次。締造出這份數據的,除了龐大的用戶需求,自然離不開資本這枚助燃劑。
單看融資規模,成立兩年半的ofo經歷了多達七輪的融資,身后集結了DST、滴滴出行、中信產業基金、經緯中國、Coatue、金沙江創投、東方弘道、真格基金、天使投資人王剛、順為資本等資本大咖。與ofo同處第一梯隊的摩拜單車亦是如此,已經收獲愉悅資本、熊貓資本、高瓴資本、華平、紅杉資本、啟明創投、騰訊等的投資。雙方的投資人加起來超過20家。
這個被貼上“資本吹起來”的標簽的新風口,一如當年的千團大戰、打車大戰,一時間甚囂塵上。除了ofo和摩拜,入局單車領域的玩家前仆后繼,例如小鳴單車、優拜單車、小藍單車、騎唄單車、由你單車、HelloBike,以及永久等傳統單車布局的共享單車項目。
如果要用一句話來形容過去這一年的狀態,戴威說是“開著飛機換引擎”——這也是程維常說的。
不難預見,ofo“小黃車”和摩拜“小橙車”間的戰爭必將不輸當年的滴滴和快的、滴滴和Uber。今年26歲的戴威表現得性格溫和、儒雅,讓人很難將他與這場火熱的“單車大戰”聯系起來。他曾拒絕用“打斗、戰爭”一類的暴力詞匯形容即將到來的那一刻,雖然他知道,“競爭是難免的”。
從0到1
一篇題為《這2000名北大人要干一票大的》的文章,在北大內網瘋傳。
作者張巳丁是戴威的大學同學,也是ofo聯合創始人。同為自行車愛好者的兩個人在大一開學就加入了北大自行車協會,在鳳凰嶺的騎行活動中相識。
文章的內容是戴威對ofo共享單車最初的構想,“在北大招募2000名勇士把自行車共享出來,這2000個人就共同擁有了2000輛車的免費使用權,其他同學要用需要付費。這也是單車市場的分享經濟和分時租賃兩大流派的根本差異。”從一開始,戴威就堅持做平臺,“不生產自行車,只做自行車的搬運工”。
2015年9月7日,ofo共享單車正式上線。上線第一天,就涌進200多個訂單,當時戴威的第一反應是,“這事靠譜了”。走在北大校園,身邊一輛輛ofo經過,這種感覺讓薛鼎感到興奮,“當時連APP都沒有,只有微信服務號。”上線10天后,日單量達到1000多。
毫無防備下,ofo火了。但是瘋狂上漲的訂單量背后,ofo也遭遇了成長的煩惱。
“剛上線時愁增長,后來訂單蹭蹭漲,服務器又不行了。”雖然嚴峻情況不及當年滴滴快的大戰時的“七天七夜”,但是對于戴威來說,也是不小的挑戰。
最初的那段日子,他經常陪技術一起通宵。這樣的通宵持續到2016年9月初,“大學開學的時候日訂單從幾萬單一下子漲到40萬單,學校數量從30個漲到200個,整個服務器的壓力非常大”。戴威在公司旁邊的酒店開了一間房,技術通宵奮戰,困了就去睡,醒了繼續干活。整個后臺的架構全部重寫一遍,在40萬單的峰值時終于扛住了。
創業,就是不斷解決問題。當戴威發現共享單車的第一波規模紅利有限,他決定在校園投放一批自生產的“小黃車”。但小黃車的出現并不在最初的構想中,購車、開發、技術、運營等高額成本隨之而來,100萬天使融資很快就要用光了。戴威開始四處借錢。楊品杰回憶,“最后是東方弘道投了300萬pre-A輪,我們才挺過來。”
戴威稱,“整個2015年幾乎都是在借錢中度過的,直到金沙江創投的A輪融資進來。”
起初,在北大校園發現小黃車的是金沙江創投副總裁羅斌。他也是北大畢業生,回母校時發現身邊有小黃車頻繁經過。
戴威清楚地記得,那是2016年1月29日,ofo日峰值訂單接近兩萬單,一個自稱是“投資人”的人打電話到ofo客服。戴威第一反應是,“這位羅先生絕對是騙子”。當時他對融資這件事已經喪失信心了。他本打算春節后再啟動融資,但還是抱著懷疑的態度回了信息,“感謝關注,有機會上門拜訪”。
意外的是,對方秒回,“明天早上10點,國貿三期56層。”在金沙江創投辦公室的那次見面,是戴威和朱嘯虎的第一次見面,也成了改變戴威和ofo的重要時刻。
二十多分鐘的談話中,“每天的使用頻率是多少,未來的市場規模和成長空間有多大”,都是朱嘯虎最關心的問題。戴威回憶,金沙江創投最初給的估值并不高,和他的預期有一定差距,“我們當時的預期是1億人民幣估值,但最后打了六七折的樣子。”
按照朱嘯虎的風格,在敲定投資之前,圈里的共享單車都研究了個遍,“有些模式太重了,互聯網要靠輕模式迅速占領市場,以后再慢慢做重,這是互聯網的一貫打法。戴威的思路很清晰,而且很多打法都很young(年輕化)”。
第一次見面后,戴威并未著急做決定,“我和巳丁當時還是比較淡定的”。走出金沙江創投辦公室,兩個人都不說話,站在國貿三期地下一層的圍欄邊,拿出手機百度“Allen(朱嘯虎的英文名)、金沙江創投”,發現“這個基金還挺厲害,這個人也挺牛”。去之前,戴威并不知道會見到朱嘯虎,更不知道見面后的Allen就是這位滴滴的早期投資人。
回到公司,戴威又咨詢了當時在機構實習的大學同學,得到的回復都是,“金沙江是你們這個階段能找到最好的投資人”。第二次見面后,雙方簽訂了融資意向。
雖然過去的一年時間里,戴威所帶領的ofo迅速完成了七輪融資。但他坦言,“我依然不是一個擅長融資的人,我的判斷主要基于雙方的價值觀是否有認同感,但這不是一個常規的融資辦法。尤其是在B輪融資的時候,我們選擇的甚至不是價格最高的那個,而是和公司的感覺最像的那個。”這樣的融資邏輯,聽起來似乎有些任性,其實不然。
在ofo聯合創始人兼COO張嚴琪看來,在ofo幾乎很少有純憑感覺做決定的事,有了感覺之后會把這個感覺的內容分析清楚,有時對有時錯,但是這個感覺需要有,不能無感,這是在戰斗中鍛煉出來的。
“商業競爭就像下棋,對方下一步你下一步,你很可能因為對手的動作而改變,這是動態的。”ofo聯合創始人兼COO張嚴琪說。
ofo雛形
ofo共享單車并非戴威的第一次創業,在此之前悄然失敗的騎游項目,發起時間在2013年7月,也就是戴威大學本科畢業那年。
他拉來張巳丁和薛鼎算了一筆賬:20萬買一輛車租一天能賺300塊,要租1000天才能回本。2000塊錢買一輛山地車租一天100塊,20天就可以回本,這個比租車賺錢多了。但是想法并未成行,三個人聊了兩次之后,戴威就開始了青海的支教工作,但是關于創業的討論并未結束,甚至ofo這個名字就是戴威2014年2月在青海注冊的。
名字的由來也經歷了一番波折,從騎百客到7bike、17bike到最后放棄英文和諧音,選擇象形ofo,因為戴威覺得,“自行車是全球通用的語言”。
從青海回到北京,戴威和張巳丁、薛鼎三人正式籌備創業。戴威記得很清楚,“ofo的一號員工是薛鼎的高中同桌,以前是制藥廠做藥檢的。挖不到別人,只能挖他。”沒有成熟的創業模型,戴威幾個人懷揣對騎行這件事的癡迷,就這樣上路了。
2014年,他開始做騎游項目,組織大家晚上八點鐘從海淀黃莊騎車到天安門,一路20多公里。期間他還嘗試過很多與騎行有關的項目,比如高端山地車以租代買等等,但騎游是主營業務,而且在2014年年底拿到了100萬天使投資。戴威說他做夢都沒想到。
可是不到半年,100萬花光了。在2015年4月這個資本火爆的時間點,戴威用了三個月時間聊了幾十家投資機構,沒有一家肯投錢給他,“公司有10個全職員工,我連工資都發不出來了。”戴威說,那是他最迷茫、最睡不著的一段日子。
“當時比較作,拿到100萬融資覺得自己太有錢了,就開始效仿滴滴搞補貼。”戴威回憶,ofo騎游做了環臺灣島、環海南島幾個團之后就想規模化發展,在廣州、深圳、廈門等這些旅游城市做地推,與租車行合作發展一個用戶送一瓶脈動。沒想到,地推團隊不到一個月談了三四百家店,每天補貼就要三四萬塊錢,100萬很快就沒了。
每天被鋪天蓋地動輒上千萬的融資消息沖擊著,戴威整個人變得很浮躁,“市場很熱,所有人都在融錢,為什么我們不行?”眼看公司賬面只剩幾百塊錢,要么死,要么變。戴威慌了,但他并未把這種負面情緒傳遞給其他兄弟。
“不到最后一刻,還是不太想放棄。”薛鼎找戴威商量,決定把環青海湖項目做到極致,團隊自負盈虧,總部不用管。帶了三個兄弟和幾萬塊錢,薛鼎在青海租了個一室一廳的小房子,用了一個月時間把沿青海湖所有的民宿、餐廳、自行車店、保障車、應急救援全談下來了,最終把價格壓到4天環湖游299元。
就在薛鼎準備大干一場的時候,千里之外的戴威正在問自己,“我身邊真正存在的痛點是什么?”他最終找到答案,丟車。以他自己為例,本科四年的丟車經歷多達五次,這是每個大學生都逃不過的魔咒。戴威做了一個大膽的設想,“最方便的就是出門看到車就可以騎,騎到哪放下就可以不管了。”
2015年5月12日,戴威對這個日子記憶深刻。午飯后,他和張巳丁在公司附近遛彎,隨口說出了自己的設想,沒想到兩個人一拍即合。他隨即打電話給遠在青海的薛鼎,三個人的想法更是不謀而合。決定了,轉型。
就在戴威還在思考如何說服青海那邊的兄弟回到大本營重新再來的時候,晚上十一點多,薛鼎一個電話打來,四個人已經連夜出發往北京趕,“兄弟們都是歸心似箭,打電話的時候已經快到蘭州了。”三天后,勝利會師。
回到北京,薛鼎、戴威和十來個兄弟喝了頓酒。酒桌上的話都已經模糊,薛鼎只記得那晚大家都喝多了。當時,所有人對于成功也是模糊的。
創業初心
與戴威一起遠赴青海支教的楊品杰現在也是ofo聯合創始人,他見證了ofo從騎游到共享單車的進化全過程,但是他對騎游項目一直不怎么感興趣,“我覺得騎游這個市場有點小,而且做旅游的上游才賺錢。”到了2015年5月,ofo賬上只剩下四百塊錢,楊品杰似乎感覺到戴威轉型的決心,“老戴要想折騰點什么事情,一定會往死里磕。”
當年從青海回京的路上,楊品杰曾問戴威,考公務員和創業你選擇哪個?戴威想都不想,“創業”。
ofo聯合創始人楊品杰最自豪的是,2015年年初百度搜索“共享單車”,什么都搜不到;但是現在一搜一大堆。
本科畢業那年,戴威“先斬后奏”,做出了一個家人都反對的決定——去青海省大通縣東峽鎮支教,而且他選擇的課程是數學。他堅信,“所有問題最終的本質都是數學問題。”
2013年8月26日,戴威和三個小伙伴到了青海。
在那里,戴威感受最深的是冬季沒有水,也沒有暖氣,只有冰山融化的水。最冷的時候零下二十五六度,晚上蓋三床被子,穿三雙襪子穿著衣服睡,屋里比屋外還要冷。“長這么大,從來沒有這么冷過。”東峽鎮的艱苦程度,讓戴威始料未及,他講了一個故事,當地老師給他蠶豆一樣的食物嚼著吃,戴威含在嘴里嘬了好長時間,才把一顆豆子吃下去。
東峽鎮到縣城17公里,到西寧市區42公里,多山路,崎嶇難行。一輛山地車成了他往返鄉鎮和縣城17公里路的唯一交通工具。周末到縣城吃上一頓德克士,是戴威難得的幸福時刻。楊品杰回憶,第一次去縣城,兩個人吃了160塊錢,戴威一個人就吃掉了143塊。
正是那段經歷讓戴威感悟,“騎行是一種最好的了解世界的方式。”2014年4月,戴威注冊公司決心創業。
北大附近的那間金和茶餐廳,是戴威與創業這件事的“第一次親密接觸”。
2010年的時候,戴威讀大二。在北大光華管理學院就讀的學生,骨子里都有一股“怎么著也要折騰點事”的勁兒,戴威也是一樣。但他回憶,當時自己對于“創業”這兩個字眼的認知非常模糊。
與那間茶餐廳的相識源于一張“糊涂卡(SmartCard)”,類似于團購的雛形。剛上大一的戴威就加入了全球最大的學生商業社團聯盟“SIFE”,負責拓展海淀橋片區的商戶加盟,在北大學生中間發行的糊涂卡可以到店消費打折,此間結識了金和茶餐廳老板。
當時老板正處于經營低谷期,開業一年多一直在賠錢,戴威又發現自己和同學每晚做PPT、頭腦風暴都要去清華附近的24小時咖啡廳,北大附近并沒有。于是,他和老板商量,“晚九點到早九點歸我,白天歸他。”他買了幾個插線板、臺燈,把自家的路由器搬過去,把附近酒店大堂的網線拉過去,大概五千塊錢就打造了一個24小時刷夜學習的地方。
開業時間選在期中考試前夕,第一天免單。讓戴威意外的是,一下子涌入幾十人,整晚爆滿。此后,每人每晚收12塊錢通宵費,最夸張的時候,要提前三天才能訂到座位。更讓戴威興奮的是,當時雇了一個人看夜場,解決了一個社會就業問題。這次“初體驗”持續了半年時間,之后的經歷曾被多家媒體報道,戴威從學院干部晉升為北大學生會主席。那段日子,他并未放棄創業的念想,只是換了一種表達方式。
楊品杰清楚地記得,戴威競選學生會主席時的主題就是,學生會產業化。按照戴威的理論,“大家畢業以后去找工作,如果是兩個一模一樣的人,一個創業失敗過,一個沒有創業過,公司肯定選擇經歷豐富的。”
戰斗意識
今年1月15日,楊品杰接到母親電話,“你看《新聞聯播》了嗎?摩拜創始人見總理了。”
他把這個消息告訴戴威,兩個人找了一個茶館開始復盤。楊品杰回憶,“那段時間負能量有點多。”
熟悉戴威的人都說,他是一個抗壓能力很強的人
他跟戴威說,“老戴你最近有瓶頸了,沒有新主意提出。”戴威說他,“最近沒有深度思考,工作太流于瑣碎了。”最后兩個人都找到了問題的節點,也找到了情緒的出口。
熟悉戴威的人都說,他是一個抗壓能力很強的人。但是短短一年時間里,ofo的員工數量從15個人急速上漲到800多人,單看去年9月C1輪融資之后,就增加了600多人。這樣的速度讓戴威既興奮又焦慮。
楊品杰說,有一段時間團隊在思想上遇到了瓶頸,沒想好到底應該怎么發展。公司從幾十個人,到一百多人,再到現在的八百多人,從一開始天天聚會,到后來坐四五桌,到現在都坐不下了,大家如何求同存異,統一思想?前段時間ofo內部組織了“使命愿景價值觀”的討論,最后定的愿景是,ofo要成為一家影響世界的中國企業。
人才,是他現在最渴求的財富。去年11月,張嚴琪加入ofo。生于1986年的張嚴琪,曾經的標簽是“Uber全球最年輕的區域總經理”,負責中國優步30個城市的業務。加入Uber之前,他是中國銀行總行的外匯交易員,2014年成為中國優步的前五位員工之一。不到兩年時間,他先后將成都、北京的月訂單量做到全球第一,在成都從滴滴手中搶到30%的市場份額。
2016年9月,四川會館。戴威的生日會上,張嚴琪隨朋友一同參加,是兩人的第一次碰面。
張嚴琪回憶,“我預期戴威應該是90后的模樣,沒想到很成熟,溝通起來很順暢。更重要的是,我對共享單車這個行業感興趣,兩人的思維方式很像,如果我來做的話也會那么做。”閑聊下來,兩人有很多一拍即合的感覺。
彼時,滴滴、優步中國合并不久,張嚴琪正在滴滴負責汽車后市場業務。但他很快發現,這個領域不足以讓他感到興奮。有了加入ofo的想法,張嚴琪征求程維的意見,“程維對年輕人創業都是抱著支持的態度的。”當時,滴滴投資ofo還未敲定。在張嚴琪看來,“這是一個巧合”。
當被問及從滴滴到ofo的原因時,張嚴琪說了四點,“共享單車未來的市場規模和戰斗規模將超過滴滴和優步中國;平臺型的商業模式很有想象力;創始團隊的理念很專注,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情是我很認同的;戴威對數字很敏感,所有商業決定都是數字驅動的。”
加盟ofo,也符合張嚴琪“開拓者”的風格。“我更多的感受是一種興奮,比如你明天有一場演出,有可能會忘詞,但是你還是很興奮,因為你并不知道觀眾會怎么樣,你只知道你有一個Show,這個Show沒有人看過。這是一種隱隱約約的興奮。”除了自己的興奮感,張嚴琪還帶來了優步中國的老同事們,“有運營、法務、戰略,還有以前Uber最大城市的總經理。”
在戴威看來,張嚴琪給ofo團隊帶來的不僅是人才,還有“戰爭意識”,“ofo之前的團隊是沒有戰爭意識的,都是獨立決策的。在競爭局面里需要有博弈,制定策略也要顧及對手的打法。我們討論一個問題,他會說如果對手這么做怎么辦。現在,我們會做沙盤推演,如果其他人這么做,我們怎么做。”
張嚴琪的戰斗經驗,得益于當年滴滴和Uber的戰爭,他說,“就像是下棋,對方下一步你下一步,你很可能因為對手的動作發生改變,這是動態的。這就像是格斗,在家打沙袋你永遠都可以贏,也可以有很多花拳繡腿的動作,但是真正的格斗是ugly的。打過仗的人和沒有打過仗的人,對事情的理解是不一樣的。”
采訪程維的時候,身邊人評價他有一種“合并夢想”的本事,楊品杰說,“戴威的身上也有這種魔性,能聚攏一幫牛人。”
拉楊品杰入伙,戴威只用了一頓火鍋的工夫。但是戴威從不打無準備的仗,楊品杰笑稱,“都是套路”。
2015年9月,張巳丁那篇《這2000名北大人要干一票大的》風靡之時,楊品杰也是ofo的用戶之一。到了年底,ofo的天使投資人組局,戴威和楊品杰都在場。就是在那場飯局上,楊品杰在醉意間被成功“洗腦”。
楊品杰回憶,戴威給他看了兩段視頻,其中一個已經忘記,另一個是日本的廣告片《人生不只是馬拉松》。鏡頭中有一堆人在跑馬拉松,突然鏡頭停止,大家四散跑開,有的去結婚了,有的去看電影,有的去養貓。“表達的意思就是,實現人生價值的方式多種多樣。”楊品杰嚎啕大哭,“在那個時間點,非常戳我(的淚點)。”讓楊品杰最有成就感的是,2015年年初在百度上搜索“共享單車”,什么都搜不到;但是現在一搜一大堆。
舍命狂奔
天剛蒙蒙亮,張師傅已經將數十輛小黃車排在望京地鐵口。這樣的搬運,每天都在重復。
地鐵、公交站、小區門口,北京幾乎每一個人流集散地,都有小黃車和小橙車的身影。原本分別盤踞北京和上海、校園和城市的兩個共享單車玩家ofo和摩拜,去年8月份在北京戰場正面交鋒。
2016年4月22日,摩拜單車正式在上海試運營,同年8月開始在北京投放,掃碼、無樁、電子鎖等設計迅速引爆媒體、社交平臺,共享單車的概念旋即在街頭巷尾被熱議。
我問戴威,“當時壓力大嗎?”
他笑笑,“當然啊,之前一年都是默默在學校做,從來沒有競爭過。從去年9月份到現在四五個月,我第一次感受到互聯網競爭的慘烈,太多事都是被推著往前走。”摩拜驚現北京街頭,ofo走出校園的腳步瞬間提速。戴威反思,“最初想要做到2000個學校再做城市的策略是錯誤的,競爭讓我們很快糾正了這個問題。”
時間拉回到“海淀小黃車”的2016年3月份,戴威有些后悔,“當時已經布滿大街小巷了,為什么不能放開讓老百姓用呢,我們當時沒有意識到城市用戶有這么強烈的需求。”如果那個時間干脆放開,或許ofo會發展更好。楊品杰說,當時確實沒有想到城市用戶的勢能那么大,現在有些后悔,“進城市晚了五個月”。
但戴威的生存法則是,“發展才是硬道理”。尤其是創業階段的公司,與大公司相比,制度不健全、缺人才、文化不完善等等都是問題,這種狀況下沒有增長,肯定得死。用他的話說,“一快遮百丑”,創業解決問題的辦法,就是舍命狂奔。
除了正面戰場的交鋒,資本戰場也并不平息。此前有媒體報道,ofo和摩拜在2016年9月的融資僵持了半個多月。
一位投資人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稱,“2016年9月,整個資本市場的觀望情緒比較大,投資人分別見了ofo和摩拜,但都不敢出手;而兩家公司也很難受,因為雖然見了很多投資人,也有人表示興趣,但真正白紙黑字敢投的不多。”滴滴當時也在猶豫要不要自己做,短途出行是其在出行領域覆蓋的盲點。當時,投資人認為最大的風險就是滴滴投資摩拜或者滴滴自己做。
滴滴會不會自己做?這也是朱嘯虎被問的最多的問題。作為程維和戴威的“紅娘”,朱嘯虎稱,“當初我們投ofo的時候就跟滴滴說過,因為共享單車這個事情是和滴滴的業務有相關性的。”他和滴滴說好,先做早期布局,等時機成熟了滴滴再進入。這個“時機成熟”,出現在去年9月26日,戴威和程維敲定融資意向也是在金沙江創投辦公室。
回憶起和程維的第一次見面,戴威印象深刻,“當時小范圍的分享會上,我坐在臺下聽他發言。直到去年9月份融資的時候,才真正聊過幾次。現在經常聊聊微信,程維在發展方向、戰略上會給我一些建議,畢竟他打過那么多戰役。”
我追問,最受益的一條建議是什么?戴威欲言又止,“這個不能說,是ofo即將要推的一些事情。”
當滴滴戰略投資ofo之后,新的問題又出現了,滴滴為什么沒有自己做?
朱嘯虎的回答是,“滴滴現在的想法像騰訊一樣,要做開放森林。程維現在不想所有的事情都自己做,打造一個開放的生態體系很重要,這樣才能做得更大。而且,自行車和汽車之間是有一些割裂的,自行車只能是一個側翼的防護。”
外界最關心的一個問題是,ofo和滴滴會打通嗎?戴威說,“肯定會。就像滴滴接入微信,是一個道理,滴滴平臺會增加一個ofo的模塊,正在開發中。”
正是在滴滴投資ofo敲定之后,其他投資人開始迅速跟進,ofo的估值一下子從此前的1.5億美元上漲到3億美元。
9月,滴滴戰略投資數千萬美元被ofo稱為C1輪融資,半個月后的10月10日,ofo又進行了C2輪融資,投資人陣容堪稱豪華:美國對沖基金Coatue、小米、中信產業基金領投,經緯中國、元璟資本、金沙江創投等跟投。機構的體量都很大,而且意猶未盡。據稱幾家機構的高層打電話來問,“能不能再多投一點?”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在資本狂熱的2015年,ofo融資艱難;到了資本寒冬的2016年,ofo卻在融資的道路上一路狂奔。在張嚴琪看來,“資本相當于催化劑,還需要本身的業務有造血的生命力。如果本身不具備造血能力或者商業模式不成立,資本很快就會看到事實。”
虎口奪食
去年10月,完成C輪融資后,ofo大規模擴展學校和城市,戴威發現,城市運營人員的壓力太大了,他決定把合伙人全部下放到主要城市去。薛鼎被派到上海(摩拜的大本營)和摩拜死磕。
他到上海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摩拜總部對面租下一間辦公室,“從北京總部出發的時候,確實是立了軍令狀的,因為上海太重要了。拿下上海的過程,就是虎口奪食。”
在校園,薛鼎的突破口是復旦大學,他用了一個月時間。“上海的推廣一開始并不順利,因為很多用戶已經被摩拜教育過。”薛鼎只能耐心解釋,“ofo已經創業兩年了,是從北京來的,有很大的數據支撐。這是個復雜的過程。”
另一位聯合創始人楊品杰被派到了武漢、廣州。他印象最深的是,“特別像打仗,每天都在數據驅動下非常緊迫。雖然大家都是合伙人,但是開周會總結的時候完不成任務還是很尷尬。老戴(戴威)會翻著筆記說,你上周新增用戶是多少,沒有完成任務啊。”每個月幾千塊錢的工資,楊品杰基本都拿來請地推的兄弟們喝酒吃飯了。
當然,碰壁都是難免的。楊品杰回憶,“一開始我們介紹ofo的項目是北大的,發現人家根本不在意,干嘛要支持北大?后來,我們找到志愿者團隊或者學生社團,以項目的形式推進學校。”他本以為武漢大學全是坡,不可能有人騎車,但最后發現,武漢大學學生用車很瘋狂,校園里看不到停著的小黃車。小黃車壞了找到修車點之后,等20分鐘修好再騎走。
張嚴琪說,ofo進城市的方式也不是一股腦沖進去,10月份在北京上地、上海楊浦區投了一點點車測試,這在商業上是非常穩健的做法。后來發現,數據增長非常好,ofo才開始正式進城。
從北京一路狂奔,如今小黃車已經遍布全國近40個城市。戴威的開城邏輯很簡單,第一步先把省會城市開了,第二步選擇哪個城市交給區域經理決定。這樣的邏輯與當年的Uber中國相似,“三個人一座城”。
熟悉戴威的人都說,他對數字十分敏感。采訪中,他對時間和數據的記憶準確到驚人。在ofo共享單車上線那天,戴威就算好了數學模型,雖然從學校逐步拓展到城市,但是基本的數學模型并未改變。在城市中多了押金這個新的變量,定價機制發生了變化,但并未影響核心元素。
從機械鎖和智能鎖、實心胎和空心胎,如今兩家的產品形態在競爭中日益趨同。對此,張嚴琪認為,“在產品上確實是接近的,但模式相差很大。ofo是一個開放平臺,車型會越來越多,來源于全世界各個國家的生產商。這個區別就像寶馬做了一個APP可以打車,但只能叫來寶馬,叫不了奧迪,但是Uber可以叫到幾乎所有的車,甚至可以叫飛機游輪,這是本質的區別。”
國內的單車大戰戰局未定,戰火已經蔓延到了海外。ofo啟動出海,對于戴威來說,出海這件事從創業第一天就在腦子里。幾年前,他在巴黎從凱旋門去埃菲爾鐵塔,走路太遠,想租公共自行車又用不了中國的信用卡。相似的狀況發生在很多國家和城市。戴威最近看到了一份行業報告,全球70%的人會騎自行車,也就是50億人,這是一個龐大的人群。這更加堅定了戴威國際化的野心,“以共享單車這件事來說,全球不可能有企業打得過我們,全世界80%的自行車是中國生產的,我們的成本優勢特別大,還有很多排他的產能。”
“現在談競爭還太早,是大戰的前夜。”張嚴琪的判斷是,3月份以后戰斗的味道就要出來了,真正的大戰在6月份以后。“到時候你會感覺到,硝煙四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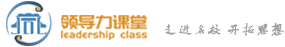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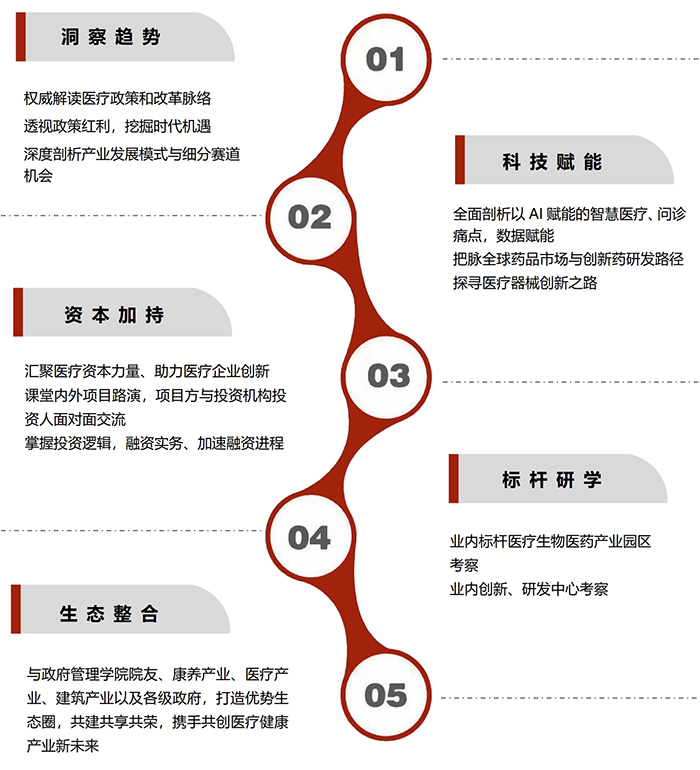






















 加多寶
加多寶 IBM
IBM 摩拜單車
摩拜單車 vivo\oppo
vivo\oppo 中興
中興 GOOGLE
GOOG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