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幾天前舉行的一場企業戰略研討會上,客戶熱議的話題是華為公司在遭到美國的技術封鎖后,啟用了醞釀十年之久的備胎計劃。
除了對華為公司的危機意識和如此長久的精心準備嘖嘖稱奇之外,大家也對未來全球供應鏈安全和技術封鎖的嚴峻前景深深擔憂。
制定業務連續性計劃(Plan B)十分必要
事實上,這次在美國政府要求下,西方科技企業對華為的斷供事件,引起了這些客戶在內的眾多科技企業的極大不安,很多企業已經開始著手制定自己的B計劃(Plan B),也就是業務連續性計劃。
記得在去年年初的時候,我就曾經向我的一些客戶,還有在我任教的商學院聽課的學生提出了預警,提示大家應該做好自身的業務連續性計劃。
但是那時,中美貿易戰的苗頭剛剛出現,而且中方的反制立場非常明確,很多人認為美國打貿易戰只是為了討價還價,在國家層面上應該可以與美國達成一致。
因為當時的各種條件和前景看起來還比較樂觀,于是有的企業家笑話我過于杞人憂天,看待世界的前景過于悲觀。
他們的理由也很充分:中美經濟已經深度融合,彼此相互依賴,尤其在技術方面,如果美國向中國發動技術封鎖,受害的將是雙方,美國政府難道不為自己的企業考慮嗎?
在當時,我就指出他們的看法過于天真了。
因為此次美國對中國發動的貿易戰也好,技術戰也好,其深刻的背景就是美國政府對中國持續發展所帶來的對美國地位挑戰的深度擔憂。
更重要的是,美國的精英階層無論是兩黨,還是政、學、商界,都在遏制中國這個問題上達到了高度的一致。
在這樣的大環境下,美國出手和出臺任何極限的施壓措施都是有可能的,我們不應該把自己的命運放在對未來的期望和幻想之上。
事實證明,一年多來中美貿易談判打打談談,到今天已經被美國升級到了對像華為這樣的中國科技龍頭企業的技術封鎖和全球打壓的嚴重階段,同時還有若干家中國科技企業也可能被放在科技禁運名單中。
在今天,如果還有哪家企業認為制定備胎計劃,或者叫業務連續性計劃還是杞人憂天的話,那也就真的是無話可說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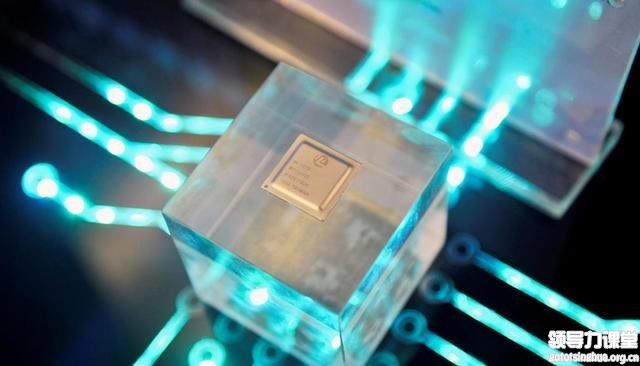
華為海思的芯片和半導體備胎計劃,源于他們深深的憂患意識和對未來中美科技博弈可能遭遇沖突的提前預期,在十年前就開始著手,打造在科技斷供之后極限情況下的自身業務連續性計劃。
這一未雨綢繆之舉,讓華為在今天依舊有底氣頑強地生存下來,并且繼續引領在5G時代的技術優勢。
今天中國的科技企業,特別是依賴于美國技術和美國市場的科技企業,已經對此感到了深深的寒意。
特別是對那些中小型的科技企業來說,自身研發能力比較弱,依賴于美國的芯片、軟件,甚至工藝授權,對此如何應對,已經是一個非常讓他們頭痛的問題。
我的一位在機械電子領域的客戶,在去年就曾聽從了我的建議,開始著手制定自己的業務連續性計劃。
首先,他們將自己的業務進行了重新的拆解,重點開始關注于高附加值的業務,并且將出口市場從美國單一市場分散到美國和歐洲,強化了在美國市場之外的合作伙伴布局。
同時,為了應對高關稅對以中國基地出產的產品阻礙,他們已經著手在東南亞地區尋找代工廠建設和合作方。
雖然外匯管制使得他們的建廠計劃受阻,但是備份的生產伙伴已經尋找到了。
所以在今年我們開始討論他們的業務連續性計劃準備情況時,這位董事長感覺比去年輕松了一些,至少在美國當前的貿易高關稅壁壘下,甚至在未來的技術封鎖情況之下,他們應該還有生存的空間。
制定業務連續性計劃(Plan B)應至少著眼于三個方面
首先是客戶群的分布,要盡量讓自己的客戶群分布多元化,不能夠只單純依賴于美國市場。
將客戶群盡量從美國市場分散開,分散到東南亞、歐洲、中東乃至南美市場,以及重新審視中國市場自身的機遇,將是業務連續性計劃第一條考慮的重點。
其次,需要對供應鏈的構成進行認真的審視,要設想一種極限場景,甚至是類似今天華為所遭遇的情景,當所有來自美國和他們西方盟友的技術對中國企業進行封鎖的時候,還有沒有生存的可能?替代方案是什么?

雖然不是所有企業都處于高技術的關鍵領域,并且會受到美國的強力打壓,但是美國對很多重要技術的封鎖,將使得很多具有高技術雄心的企業在基礎芯片、生產設備、檢測儀器、關鍵零部件,乃至工業軟件等方面遭受巨大的不確定性。
因此對此認真地制定備份方案是非常重要的。在我看來,這一窗口期可能還有半年到一年的時間,在這段時間內做好充分的準備至關重要。
最后,關于制造基地的選擇,就像我那個客戶一樣,已經開始在東南亞地區尋找若干代工生產伙伴,來避開美國的關稅壁壘。
如果美國對中國的所有產品全面征收關稅的話,對于那些客戶在美國的企業,將生產制造的一部分搬離中國可能是不得已的選擇。
如何在這個階段有效地規避風險,同時在收益和風險之間找到均衡,需要在現在就做出決策。
對于個人來說,我們的日常工作軟件,這些現在嚴重依賴于微軟、蘋果和安卓系統,尋找各種開源的替代方案和其他專業化替代方案將是必須的。比如將個人資料文檔逐漸轉移到類似于WPS這樣的平臺上,就是為了預備未來的不時之需。
每個企業都應思考制定災難備份計劃(Plan C)
比業務連續性計劃更嚴重的是災難備份計劃,這是每個企業應該思考的C計劃(Plan C)。
在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的創始院長格雷厄姆·艾利森得名著《注定一戰: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嗎?》一書中,就提出了中美之間有可能爆發戰爭的若干種可能場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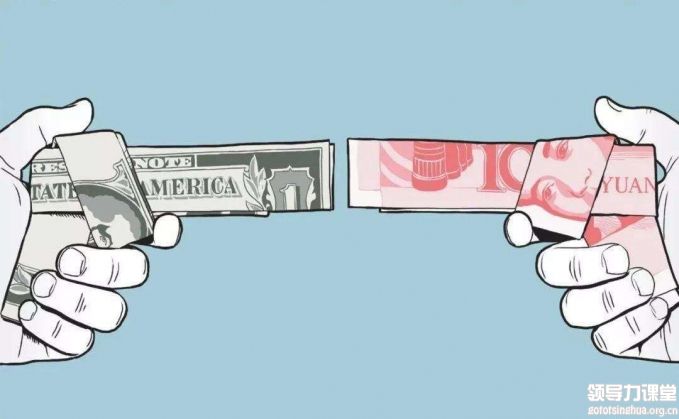
今天讀起來會發現務實的美國學者絕不避諱中美這兩個大國,即便是核武器大國之間爆發戰爭的可能性。
因為在目前復雜的背景條件下,任何火花性的事件和外部催化劑都可能導致事件不斷升級,以至于達到不可控的地步。
在歷史上也有大量的事件可以加以證明,在作者研究的16個新興大國和守成大國之間的較量中,有12次導致了戰爭,只有4次因為特殊的原因避免了戰爭。
所以避免“修昔底德陷井”的困境是一個良好的愿望,但是思考可能的戰爭風險也是每一個企業需要認真考慮的外部環境的變量。
在這本書中,埃利森提出了若干種有可能使得事態向戰爭方向發生的場景,包括海上的意外碰撞以及因此出現的事態升級、臺灣尋求獨立、第三方挑起的戰爭、朝鮮問題引發的戰爭,以及因為對經濟沖突的管控不當而導致的從經濟沖突到軍事戰爭的可能性。
說老實話,這本書中的各種情景假設在若干年前讀起來還覺得是大開腦洞的暢想,而今天看起來倒真的有可能是我們需要認真面對的潛在可能了。
對于C計劃,也就是災難備份計劃,就不需要再認真考慮所謂的業務連續性了,因為一旦出現這種極端的戰爭情況,商業和業務對于很多公司來說將是不得不停止的選項。
而此時,更多是要考慮人員的安全和在大沖突背景下企業乃至人員的生存問題。所以作為災難備份計劃來說,需要有幾個關鍵點認真加以厘清。
災難備份計劃(Plan C)的關鍵點
首先,如何確保企業中人員的安全?對于地處一地的企業安全和疏散來說,這不是一個太困難的事情。
如果分處在不同地域,特別是分處在全國乃至全球不同地方的企業來說,人員的安全和疏散將是一個具有挑戰性的問題,因為各個地方所處的安全環境不同,面臨的挑戰也不一樣。
例如,居于中國沿海地區的企業,要假想各種因為臺海危機或者南海危機而導致的地區沖突的風險,而地處內陸的企業這方面的危機防控的方式就和他們不同。

其次,企業雖然是一個經營單位,但是也承擔著相應的社會責任。如果事態繼續升級,每一個負責任的企業和企業家也應該對自身的員工人身安全和家庭安全承擔起最大的責任。
在各種急救用品的供給、糧食安全和人員安全方面做出一些提前的預計。
關于此,我在去年就曾在微信公眾號的文章中提示過。今天在這里繼續提出來的時候,在那次研討會上也遇到了與會一些企業高管的質疑,他們覺得事態應該不會發生到如此地步。
我依舊用我去年的觀點來回應他們:
不要用自己的美好期望來預測這個世界,我們所能做的就是看到事態的發展和趨勢,來做最壞的打算,從而能保全自己,幫助他人。

在今天的環境下,每一個企業去認真思考自身的兩個應急計劃,業務連續性計劃(計劃B)和災難備份計劃(計劃C),不再是無稽之談,而是非常關鍵的戰略準備。
所謂有備無患,每一個人如何選擇,就看每個人自身的洞察力和對未來的預期了。





























 加多寶
加多寶 IBM
IBM 摩拜單車
摩拜單車 vivo\oppo
vivo\oppo 中興
中興 GOOGLE
GOOG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