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幾家互金巨頭和幾家大型銀行相繼簽署合作協議。就商業銀行而言,在行業周期的下行階段發力轉型,決策層固然有強烈的緊迫性,但似乎未找到明確的方向,而執行層則面臨增長壓力和人才流出的雙重難題,一時也無暇顧及轉型。轉型不易,開放合作,似乎便成了不得已的選擇。
這幾日,幾家互金巨頭和幾家大型銀行相繼簽署合作協議,在市場中賺足了眼球,有人甚至戲稱金融行業步入“美蘇爭霸”的新階段,好不熱鬧。不過,各行各業,傳統巨頭的轉型向來不易,成功者寥寥。
就商業銀行而言,在行業周期的下行階段發力轉型,決策層固然有強烈的緊迫性,但似乎未找到明確的方向,而執行層則面臨增長壓力和人才流出的雙重難題,一時也無暇顧及轉型。轉型不易,開放合作,似乎便成了不得已的選擇。
轉型的終點在哪里?
在行業下行周期和新金融業態蓬勃發展的雙重影響之下,對傳統銀行而言,轉型是實現可持續增長唯一正確的選擇,但轉型的方向是什么?終點又在哪里?似乎沒人能講得確鑿無疑。方向不明,轉型就先失敗了一半。
就目前來看,大銀行的轉型方向大致是“線上互聯網化+線下網點智能化+走出去+綜合經營+交易銀行+科技驅動”,幾乎每一點都對應一到幾個部門;對于中型銀行而言,去掉“走出去”;對于小型銀行而言,再去掉“綜合經營”。
大體上看,除了規模的不同,轉型方向仍然是趨同的,可見,既便每家銀行都能轉型成功,結果依舊是同質化的。
問題來了,引致同質化的轉型方向真的對嗎?
沒錯,一直以來,銀行的經營都沒有擺脫同質化,但大家都能和平共處。不過,步入移動互聯網和科技驅動的新時期,基于同質化的和平共處恐怕不行了,根本的原因在于線上APP代替線下物理網點成為戰斗的一線。
戰斗力再強悍的網點都存在天然的物理邊界,而再小的APP在互聯網上都是無界的,競爭從有界到無界,同質化便沒有存在的空間。
所以,如果轉型的結果帶來的是同質化,那么轉型的方向便是錯的。什么才是正確的方向?基于自身稟賦,每家都有不同,才是理想的狀態。但實際上,金融產品就那么幾種,要充分做到差異化不容易,尤其是數千家機構的差異化,幾乎不可能。
既然未來的市場容不下同質化,數千家機構又不可避免要陷入同質化,也意味著未來的市場容不下數千家機構。并購重組,恐怕會成為未來行業發展的必經階段。
對于業內大多數中小型銀行而言,若找不到差異化方向,可能或遲或早都會成為被并購的對象;而對于大中型的銀行巨頭而言,唯有轉型一條路可走。
但是,為轉型找到方向談何容易。2016年9月,美國《連線》雜志曾發表文章評價科技巨頭的轉型之難,重要的一點便是方向問題:
“戴爾、EMC、惠普和英特爾近些年學到的教訓就是,硬件公司變成軟件公司并非易事。但事實上,軟件領域的公司也犯了類似的錯誤。谷歌和微軟學到的教訓就是,軟件公司變成硬件公司也并非易事。近幾年,谷歌收購了手機廠商摩托羅拉移動,但沒過多久就將它轉手給了聯想。微軟則在減記收購回來的諾基亞手機資產。”
未來已來,只是尚未流行。大中型銀行轉型的方向在哪里?肯定是上述“線上互聯網化+線下網點智能化+走出去+綜合經營+交易銀行+科技驅動”中的一種,具體是哪一種或哪幾種的組合,各家銀行各有不同。
當然,有一點可以肯定,如果把上述所有方向都當做轉型的目標,大而全,不聚焦,約等于沒有目標,是不可能成功的。
從目標到落地:執行層面的障礙
既便選擇了正確的方向,執行層面也會面臨落地的難題。對銀行而言,促轉型的同時還要穩增長,在決策層,二者同等重要,不能偏廢;在執行層,轉型很重要,但增長更重要。究其原因,決策層關注中長期可持續發展,關注發展潛力,而執行層更關注短期績效,關注考核指標的完成度。
那么轉型能否納入考核指標體系呢?可以,但權重不能太高。一方面,在短期內,現有業務和舊模式才是增長的源泉,在競爭激烈的市場環境下,對于現有業務,一刻也不能放松;另一方面,賦予新模式過高的考核權重,往往欲速不達,基本會誘發花樣繁多的指標造假,反而打擊了踏實發展新業務的分支機構的積極性。
舉個簡單的例子,考核指標為直銷銀行渠道的理財余額,若賦予很高的指標權重,必然有很多機構動員客戶把本應柜臺渠道銷售的理財產品更換至直銷銀行渠道,左手倒右手,數字游戲而已。當然,針對考核指標體系,指標制定機構與具體執行機構的博弈要復雜得多。
更根本的一點在于,任何一種轉型,都不僅是一種經營戰略的重新選擇,更是一種利益關系的重新調整,涉及到資源和權力的重新配置,也會要求文化的重塑,自然會遭遇阻力。
就以銀行的互聯網化轉型為例,前幾年一度非常熱鬧的直銷銀行部先后沉寂,現在不得不探索設立直銷銀行獨立法人機構。中國歷史上幾大著名變法,失敗者居多,究其原因,既有既得利益者的阻撓,也有普羅大眾的“民曰不便”,前者是利益問題,后者更多是文化問題。
此外,優秀人才的流出也是個隱患。近年來,媒體多關注銀行高管的出走,其實銀行基層組織的人才流失同樣令人矚目。行業下行期,收入、職業空間與壓力的不均衡,加上互金機構的對線下渠道和三四線城市的布局,很多銀行基層員工紛紛選擇逃離,人才的流失反過來加劇了執行層面的落地難。
放眼來看,各行各業的轉型都不容易。據統計,1981年的世界財富500強企業,50%的企業跌出了1990年的榜單;1991年的財富500強企業,70%的企業跌出了2000年的榜單;2000年的500強企業,68%跌出了2012年的榜單;2010年的500強名單,48.6%跌出了2016年的榜單。此為一個例證。
如果打不過你,就與你合作
之所以需要轉型,主要是因為在新模式的襯托下,企業變得傳統。巨頭一旦被打上“傳統”的烙印,便大概率會遭遇一個悲傷的結局。
恰恰技術進步日新月異,新模式、新機構層出不窮,更多地的企業都是“被傳統”而已, 一個不小心,顛覆傳統企業而成長起來的新巨頭就變成了“傳統企業”,進攻者變成了守成者,攻守之勢異也。
遍觀科技巨頭,面對新模式的崛起,多采取“如果打不過你,就把你買下來(If you can't beat them, buy them)”的模式,無論是國內的BAT還是國外的谷歌、Facebook等等,都開啟了買買買的模式來應對潛在挑戰。
而就國內銀行業而言,買買買的模式尚不現實,也就只能采取“如果打不過你,就與你合作”的模式。
好在,隨著行業監管框架的落地,互聯網金融業態迎來強監管時代,開始強調合規經營和規范化創新,行業也逐步擺脫了新興業態的標簽,在很多方面都與傳統金融站在同一起跑線上,且進行互補發展、錯位競爭。
相似的監管框架和差異化的定位,使得互金與傳統金融機構具有了更多的合作基礎。當然,業務層面的合作會不會進一步演化成股權層面的買買買,那就是后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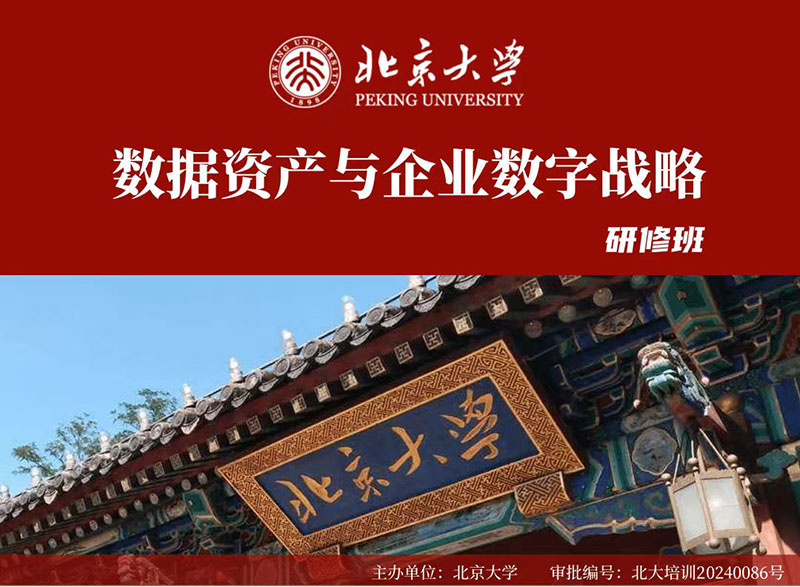
























 加多寶
加多寶 IBM
IBM 摩拜單車
摩拜單車 vivo\oppo
vivo\oppo 中興
中興 GOOGLE
GOOG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