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9月25日,我坐在美國聯合航空的空客飛機上,對于滄海桑田般的巨變感慨萬千。
曾在《財富》500強中名列第156位的貝爾斯登從神壇上掉了下來,被摩根大通收購,且整個交易是在一個周末倉促達成的。雷曼兄弟在經歷了158年的輝煌后,也陷入了破產的絕境。房利美和房地美危機纏身,最后只得被政府接管。美林證券代表了美國近一個世紀來的輝煌,最后也沒法逃脫被收購的厄運。步履蹣跚的華盛頓互助銀行差點成為歷史上面臨破產的最大商業銀行。
從一方面而言,這很正常。無論多么出色,每個組織都很脆弱。沒有最強勢者必然長居頂級的自然法則。任何人和事都可能衰落,而且大部分最終確實如此收場。但另一方面,我越來越好奇:強勢者何以會走向衰落?歷史上曾經一些最出色的公司也會從偶像標桿淪為無名小卒,我們能從中學到什么,其他公司又如何避免同樣的命運?能否及早發現衰落的跡象并扭轉局勢,或者是我們能否提前預防?
并非全無希望。通過昔日業界巨鱷江河日下的案例,我們能從中獲得很多寶貴經驗,從而更好地將其付諸實踐。領導者們可以在為時太晚前極大地提高翻盤幾率,甚至可以從一開始就避免走上衰落之路。
衰落是可以避免和扭轉的,只要企業還沒有深陷衰落的最后階段,改弦更張還來得及。強勢者可能衰落,但它們也能再續輝煌。
狂妄自大
組織的衰落就像疾病:在早期很難察覺卻很容易治愈;在晚期很容易察覺卻很難治愈。一個組織可以從外部看上去很強大,但內里卻已問題叢生、處在極速衰落的危險邊緣。
1983年12月,摩托羅拉公司最后一臺車載廣播下線,并作為紀念品被送到公司前董事長羅伯特·高爾文的手里。它并不是一個煽情的紀念品,而是在提醒摩托羅拉的掌舵人要繼續研發新技術和新產品,從而不斷實現自我更新。
可惜的是,摩托羅拉仍像大多數優秀企業一樣,沉迷于取得的成績而變得故步自封。經過多年的成功運營,到了20世紀90年代中期,摩托羅拉將年營收從10年前的50億美元猛增到了270億美元,這也使得摩托羅拉人的心態從謙遜轉為傲慢。
1995年,摩托羅拉對于推出的StarTAC款手機頗為得意,因為這是當時世界上最小巧的手機,也在業界率先推出了翻蓋手機設計。但摩托羅拉卻忽略了一個問題:當時的無線電話運營商正在將注意力轉向數字技術。但是,他們對于數字化威脅毫不在意,“有4300萬模擬信號用戶,這個市場錯不了。”
借用美國歷史學教授J·盧夫斯·菲爾斯的說法,過度傲慢會讓無知者付出代價。摩托羅拉的這種傲慢態度惹怒了貝爾大西洋等主流運營商,貝爾大西洋公司反擊說,“按你們的意思,如果我們不同意你們的條款,你們就不打算在曼哈頓賣StarTAC款手機嗎?”
可以說,摩托羅拉的沒落就是從狂妄自大開始的。作為昔日世界手機市場上的頭號霸主,摩托羅拉曾經壟斷了將近50%的市場份額,但到了1999年,其市場份額下降到只有可憐的17%。2001年時員工總數還有14.7萬人,到2003年年底就已裁到只剩8.8萬人了。
2010年10月,在46歲的印度裔工程師桑杰·賈(SanjayJha)出任摩托羅拉聯席CEO的第8個月,他覺得這家在接踵而至的壞消息中踉蹌跌落的公司終于“燃燒殆盡”了。2011年8月15日,谷歌公司宣布將以每股40美元的價格并購摩托羅拉移動公司。這家昔日手機霸主只能留在人們的回憶中了。
從1995年到2011年,摩托羅拉用了16年時間告訴世人:當我們變得傲慢自負,認為成功是理所當然的,忽略了最初成功的真正動因時,衰落就悄然降臨了。
盡管在短期內,企業原先積累的力量在短期內仍會推動它繼續前進。但是當成功者開始把自成功掛在嘴邊(“我們之所以成功,是因為我們做了這些特別的事”),而不是深入發掘、洞悉成功的原因(“我們之所以能成功,是因為我們知道為什么做了特別的事,我們也知道在什么樣的條件下,原來的做法并不管用”),那么衰落很有可能就會接踵而來。而在古希臘,人們談及狂妄自大的時候,已經暗喻一個英雄將因為過于驕傲而折戟。
盲目貪求
滋生了目空一切傲慢情緒的心態(“我們這么厲害,我們可以做任何事!”),就會無節制地追求更多更大規模、更高增長、更多喝彩、更多隨便什么被當權者視為“成功”的東西。在這種情緒下,公司就有可能偏離最初讓它們變得偉大的創造力,進入在其中并不能成為卓越者的領域。
我們來看看默克公司的例子。1995年,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雷·吉馬丁在《致股東的年度公開信》中稱:默克公司的首要目標是成為增長速度最迅猛的公司。
這讓人感到奇怪,因為默克年銷售收入將近50億美元的5種藥品到21世紀初就要失去美國的專利保護了。雷·吉馬丁面對的是,公司要通過研發足夠多的新藥以實現在營收為250億美元的基礎上同樣的增長或高速增長。對于默克這樣一個主要依靠科技研發的企業而言,實現持續高速增長,難度非常大。
然而,默克對自己的業務前景仍然滿懷信心。在公司1998年年報董事長致辭的第二段,你可以發現答案新型止痛藥萬絡(Vioxx)。到2002年年底,萬絡的銷售額已達到25億美元。
但在2004年9月中旬,對患者進行安全監測的委員會卻收到了聯邦快遞送來的“驚人數據”。默克年報中是這樣概括這一結論的:“與接受安慰劑效應測試的患者相比較,在服用萬絡一年半之后,患者患心肌梗死和中風等心血管疾病的風險會增加。”
當雷·吉馬丁得悉這一消息后,他說:“這讓我震驚萬分。”不過,在一周內,雷·吉馬丁就作出了英明果斷的決定,主動讓萬絡下架。此消息一出,默克公司的股價立刻從每股45美元急跌至33美元,一天之內總市值就蒸發了250億美元。到了2004年11月上旬,當每股股價跌至26美元時,投資者又損失了整整150億美元,這也意味著在短短6周內,默克市值已經縮水400億美元。
默克公司因為忙于擴大規模,忘記了當初成就自己卓越事業的使命。1950年,喬治·默克二世清楚地表達了公司的使命:“我們永遠都不要忘記,藥是為人服務的,而不僅僅是為了賺錢。如果謹記我們的目標,那么利潤自然會滾滾而來。”
引述這個例子的目的在于揭示,盡管自鳴得意和抗拒變化對任何成功企業都很危險,過度擴張更能揭示強勢者是怎樣走向衰落。貪求會讓你將承諾的泡泡越吹越大。直到某一天,泡泡終究會被你吹破,而且七零八碎、無可救藥。
誠然,上市公司每時每刻都面臨著來自資本市場的壓力,市場希望公司擴張規模的速度越快越好。但卓越的領導者不會以犧牲公司的長期價值來追逐增長,也不會把增長同卓越混為一談。畢竟,卓越并不一定意味著規模巨大。
漠視危機
也許,公司的衰落并非因為狂妄自大和盲目貪求,而是掌權者或領導團隊精神狀態發生了變化。具體地說,他們對負面的數據半信半疑,對正面數據則夸大其詞,把模棱兩可的數據都解讀成好消息。面對突然出現的困難,認為只是“暫時的”、“周期性的”、“不至于那么糟糕”、“沒有什么大不了的”。
在研究過程中,我們發現11家公司中有7家公司在衰落時期會把責任推卸到外部因素上。
當真力時公司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遭遇困境時,首席執行官列舉了一系列外部因素作為擋箭牌:“誰能預料到會發生水門事件?誰能預料到現在面對的大蕭條……我們突然就遭到了重創。”
真力時也抱怨來自日本廠商的不公平競爭,這種競爭使公司的利潤銳減,而且市場份額不斷下滑。即便日本廠商真有“不公平”競爭的情況,但真力時的表現就像美國汽車廠一樣,拒絕承認日本競爭對手能生產出物美價廉的產品。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方興未艾的分布式計算開始影響IBM的主營業務,IBM開始走向了下坡路。有名高管將這種讓人擔憂的趨勢坦誠地告訴了公司的其他高管,結果發現自己卻成了眾矢之的,一位說一不二的領導將這份報告扔到一旁,不屑地揮手說道:“報告中的數據肯定有問題。”
盡管IBM后來進行了改組,也加大了研發力度,但是并沒有能夠止住公司業績下滑的勢頭。到了1992年,業界將IBM比喻為一只將絕跡的恐龍。
最后,是富有傳奇色彩的首席執行官郭土納幫助IBM扭轉乾坤,他直面IBM的缺陷,在他任職的早期就向高管團隊提出了尖銳的問題:“IBM至今已經裁員12.5萬人……是誰讓他們丟了飯碗的?難道是上帝的旨意嗎?是競爭對手崛起并打敗了我們。”
企業忽視危機最后一點值得我們關注的表現,就是像走馬燈似的進行重組。1961年年底,斯考特紙業在餐巾紙、面巾紙、棉紙等各種紙類產品中都獨占鰲頭,已經成為世界最成功的消費品紙業公司。此時,寶潔、金佰利—克拉克、佐治亞—太平洋等競爭對手開始侵占斯考特紙業的市場份額。1960-1971年期間,斯考特紙業的市場份額從一半下降到只有1/3。
斯考特紙業的應對之策是什么呢?不是調整公司戰略,而是選擇部門重組。僅80年代,重組行為在4年間竟然有3次之多。
公司重組會給你帶來一種錯覺,會讓你誤以為公司正在做的事富有成效。當然,重組也是公司不斷進步的特征之一。但是面對不利的數據和跡象時,如果首選對策是重組,很有可能就是在漠視危機。這有點像是面對嚴重的心臟病或是癌癥時,你只是把家里的家具搬來搬去試圖緩解病情一樣。
任何組織都不是盡善盡美的烏托邦。所有的組織結構都有利有弊,每種組織結構都有效率不高之處。我們的研究表明,沒有哪種組織結構能遮擋任何風雨,任何形式的重組都不能讓風險和危險自行消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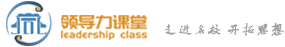



























 加多寶
加多寶 IBM
IBM 摩拜單車
摩拜單車 vivo\oppo
vivo\oppo 中興
中興 GOOGLE
GOOG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