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震,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京都大學博士,兼任上海儒學院執行副院長、中國哲學史學會副會長、上海市儒學研究會會長等職。著有《中華傳統文化百部經典·傳習錄》《陽明后學研究》《傳習錄精讀》《朱子思想再讀》《東亞儒學問題新探》等專著二十余部。
做學問要做得好,要甘愿坐十年冷板凳
一、您是如何走上哲學這條道路的?
1977年恢復高考,當時很突然,時間很緊,報什么專業沒有一個明確的方向。但是以前對歷史比較有興趣,看了一些書,就報了歷史系。讀了四年下來,覺得對于歷史不太感興趣,讀不進。還是對歷史系當中涉及到的一些思想文化比較感興趣。比方說在歷史系當中有一個傳統叫思想史這個專業,在畢業之前寫學士學位論文的時候,就寫了關于中國思想史方面的論文。寫完之后對于未來的專業、研究的方向做了一些慎重的考慮。然后就考到復旦大學的哲學系,以中國哲學為專業方向。所以從歷史跨到哲學既有一些偶然的因素,也有我個人興趣愛好的原因。
二、學哲學會覺得無聊嗎?
那肯定也有無聊的時候,特別是念古籍,那時候還沒那么大量的標點本,要從線裝本開始讀起,從頭到尾你要仔細地閱讀,肯定會碰到一些很無聊的時候。但是作為一個研究的領域跟方向,這是一個基礎的功夫。老師也再三教導我們,必須要從這個方面去著手。我們有一句俗話:做學問要做得好,要甘愿坐十年冷板凳。
三、您研究了東亞儒學、宋明理學、陽明后學,除此之外,您還有其他方面的研究成果嗎?
實際上從我專業的領域來講,我的第一研究領域是陽明心學。陽明心學研究過程當中,我發現一個現象,就是在八十年代初的時候,很少有學者關心陽明后學的思想發展情況。因為那個時候,有關陽明后學眾多大弟子的古籍版本都很難找到。因此要讀這些書,就要到圖書館去,自己到古籍部去把它找出來。我就想是不是在這樣一個比較冷的領域當中,能夠開拓出一些新的研究方向。所以碩士的論文,我寫的就是關于浙中王門的王畿和泰州學派的王艮,把這兩個人合起來進行研究。那當時在學術界,研究的人還是比較少的一個項目。
到日本留學以后,我實際上仍然是在堅持陽明后學的研究,一直研究到我拿到博士學位。因此我從碩士到博士,研究的都是陽明學跟陽明后學。研究完了陽明學跟陽明后學,同時又回到整個宋明理學,再回到朱子學,再把朱子學跟宋明理學重新打通,這個跟陽明學研究幾乎是同步進行。至于東亞儒學實際上是非常晚了,因為我2018年出了本東亞儒學的書,東亞儒學題目比較大,包括中國、日本、韓國,可能還要包括越南,但是我的研究比較集中在日本。日本研究的時候涉及到一個問題,就是如何來理解東亞這樣一個概念,而東亞這個概念歷史非常早,在19世紀末日本就開始使用這一概念。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特別是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東亞這個概念就被有些政治意識形態等等利用和歪曲。所以東亞這個概念,是一個帶有一定意識形態烙印的概念。那么我們現在21世紀,在回顧中國的傳統儒學到日本之后或者到韓國之后,他們在本土化的轉化過程當中,儒學怎么變成日本的儒學,怎么變成韓國的儒學,這樣一個問題在進行思考的時候,涉及到我們如何來理解東亞這個概念,東亞是不是一個一體化的概念等等。這里面就涉及到一些學術性的問題,比較深奧,那我在《東亞儒學問題新探》這本書當中,特別是前面的兩章,專門就文化東亞、什么叫東亞、東亞儒學何以可能、東亞儒學何以必要等等問題,展開了比較詳細深入的學術性的探討。那么這些探討可能在大陸學界,還是比較重要的一個問題探討。那么這問題探討完了以后,我們才能進入到日本的儒學是怎么一回事,韓國儒學是怎么一回事,特別是中國儒學跟韓國儒學、日本儒學,做一個跨文化比較的時候,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儒學從11世紀到19世紀末,八百多年的時間,如何在東亞的文化中站住腳跟,并且經過了一系列的傳承、轉化和創新等等。這樣一些歷史現象通過東亞儒學的研究,可以說幫助我們了解儒學是如何走出中國、如何能夠被世界其他地域的文化所吸收跟轉化,東亞儒學是一個非常典型的案例。希望后輩、希望年輕人,能夠更多地投入到這個研究領域當中去,這是我的一個愿望。
京都大學獲博士學位時吳震在京大校門留影 吳震著:東亞儒學問題新探 致良知實際上就是日常生活行為方式

四、陽明心學在日本有什么樣的影響?
陽明心學在日本的影響,實際上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是從日本返回到中國,給整個社會輿論界、政治界、學術界等等,造成了一個非常大的反響。這個反響,說句可能不是太恰當的話,實際上就是一種輸出去之后、再一次進口。這跟非常重要的幾個歷史背景有關系,一是日本方面的明治維新,中國方面就是甲午戰爭戰敗,第三個因素是中國戊戌變法的失敗。那么日本明治維新發生的時候,對中國直接的影響不是很大,中國人那時候正在搞新的洋務運動,還不知道日本明治維新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甲午戰爭被日本打敗,這對于中國的政治、文化、習俗等等整個社會產生了巨大的一個反響,泱泱大國何以被一個蕞爾小國給打敗了。因此,康有為、梁啟超、李鴻章、曾國藩等人他們搞了洋務運動,他們是要深思,除了技術上不如人家之外,是不是還有其他的原因,比如政治文化方面的原因。要進行改革,要向日本明治維新學習,這就有了戊戌變法。但是戊戌變法1898年發動還不到一百天,就失敗了。失敗了以后,康有為、梁啟超逃到日本去了。他們到了日本以后才發現,原來明治維新的過程當中,有許許多多都是陽明學的信徒。那么,梁啟超、康有為,包括后來的蔣介石、章太炎,他們到了日本以后目睹了這樣一種現象,認為日本學者的這種說法肯定是對的。因為有幾個陽明的信徒的確參與了明治維新,因此,他們把明治維新的成功一部分的原因歸結在陽明心學。
然而,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特別是進入21世紀,現在日本的學術界對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所提出的這樣一種觀點,已經提出了批評。我就舉一個例子,吉田松陰是一個非常著名的、推倒江戶幕府時代的仁人志士,據說他是讀過王陽明的書的。然后我到吉田松陰的紀念館去參觀,我去看他的生平介紹、他的生前遺物。我參觀了以后,我才比較正確地了解到,實際上哪怕就是像吉田松陰這樣一個人物,他所看到的關于王陽明的書,應當說是比較膚淺的一些東西。根據一些留下來的記載,他真正接觸到王陽明的書,實際上是進了牢里以后,在臨死之前,沒有多少時間。而在讀的過程當中,與其說他是對陽明心學有非常深的理論研究,還不如說他對陽明后學的一個人物叫李卓吾,也就是李贄,他對李贄這個人最為欣賞,覺得李贄跟他氣味相投。王陽明這本書他可能看過,但是可能在思想上、理論上的了解不是很深,更不用說他用王陽明的思想作為一種武器、作為一種思想信念、作為一種口號,提出來鼓舞社會,號召大家都去推翻江戶幕府,這樣一種現象應當說可能是不存在的。
所以現在是這樣,大陸的學術界跟日本的學術界由于割斷了很多年,日本的一些嚴肅的學術研究的著作,翻譯成中文在大陸出版的數量是少得可憐。因此我們大多數人都不了解日本學術界嚴肅的學者,對于這段歷史的研究成果跟他們的看法。我想在今后陽明學的研究過程當中,包括紹興,包括稽山王陽明研究院,是有義務跟責任把日本學術界的有關陽明學的最新研究成果,而且要最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把它翻譯過來。雖然這不是面向大眾,但是對于我們在學術界撥亂反正、在學術界把這個看法重新扭轉過來,我覺得是相當重要的,這是一個方面。當然,我們中國大陸的學者自己也有一份擔當,包括我在內,其他的一些學者應當也自覺意識到這個問題。
五、陽明先生曾經說,良知其實是在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有所體現的,這句話您是怎么理解的?
孟子提出“良知”這個概念的時候,實際上已經蘊含了這層意思。良知本來的意思是比較簡單的,什么是良知呢?良知就是在“知”的前面加一個“良”,使得自己有好的知。但問題是這個“知”是什么,在“知”的前面加一個“良”限定這個“知”的時候,這個“知”它是特指一種能夠知道好壞、是非、善惡的一種“知”,這個“知”才是真正的好的“知”,叫做良知。那么如果這樣來理解良知的話,用現在的話來講,這個“知”就是一種道德知識,不是物理學知識。道德知識就是我們是怎么做人的,我們不能夠做壞事,我們要做好事、要做好人,這就是好的知識,這就是良知。孟子又說,良知是通過不學而知的,不用通過后天的學習,良知良能是不學不慮天生就具備的一個人的道德的直覺,這是最早孟子提出良知這個概念時,所講的這些簡單的意思。
那么王陽明當然全盤接收孟子所講的關于良知的概念,但在理論上還有進一步豐富的發揮,我把它叫做良知學理論的系統。良知一方面它是根植在我們每個人心中的一個善良的道德之本心,這是基礎。但是王陽明他也知道你光這么講,普通老百姓很難接受,因此他也知道要把良知作為一種學問,叫做致良知,良知前面要加一個“致”字,他告訴我們良知每個人先天就有的,比方說“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悌,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他講過這么一段話。但與此同時,這樣一個良知它實際上就是落實在我們每個人日常生活行為當中,它是流行發用于事事物物當中。他把朱子學、程朱理學以來的有關于格物致知的這套理論做了一個通俗化的、創造性的詮釋,把格物致知等于即物窮理扭轉成隨時就地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就物得其理了,也就是知致了。當他這樣來解釋的時候,就是說我們所謂的格物致知即物窮理這樣一些知識論追求的一種功夫,實際上是跟我們的良知落實在事事物物上的這種道德的實踐、社會的實踐是密不可分的。因此致良知實際上就是日常生活行為方式,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有良知,當你從睡夢中醒過來、眼睛睜開來,你一念閃動的時候,時時刻刻你的意識是不會停止的,在你的意識活動過程當中良知就已經存在著,如果你能夠捫心自問,按照你自己的良心去做事的時候,那你就是致良知。陽明學的良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一般的老百姓、普通的大眾都能夠聽得懂,也都能夠接受的這么一個理論。
當然,如果再追問一下,良知這個概念本身是不是會是隨著時代的變化而發生變化,那么這個問題講起來又比較復雜,簡單來講,良知本身它如果是作為一個抽象的或者作為一個哲學意義上的本體存在的話,那么良知它是一個永恒的、永遠的、普遍的。但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具體的有關于良知所制定的一些道德規范,比如說16世紀王陽明那個時代所制定的道德規范,過了五百年,到現在是不是我們還會認為必須這樣做才對。這個呢,具體的道德規范應當是隨著時代的變化有所改變,這么來理解良知這個概念我覺得就比較全面。一方面是超越、是普遍的,另一方面它又是具體的,它是落實到我們今天社會的,但是可以有所創新的,不能夠很保守的。這個在研究、宣揚陽明心學的時候,千萬要注意到這一點。
六、陽明先生說過:“一念發動處即是行”,怎么來理解這句話?
我專門有過一篇文章討論這個問題,這問題涉及到知行合一的問題。知行合一現在社會上比較一般化的理解,就是簡簡單單的言行一致。你想到一些什么事情,馬上就落實在行為上去做,那就叫做知行合一了。這個呢,沒有錯,但是這個觀點你不能夠把它套在陽明學的知行合一這個命題里面,去解釋陽明學的知行合一。陽明講知行合一的這個命題,當他提出來之后在當時社會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彈。從原理上來講,知行合一這個命題是非常難理解的一個命題。難理解在什么地方呢?按我們一般的常識性的判斷,知識和行為的關系,肯定是有先有后、有輕有重,之間有時間差。用朱子學的說法就叫知先行后,沒錯。但是王陽明講知行的關系的時候,他的問題的意識、他所探討這個問題的角度,他不是在探討一個人的行為過程當中,是不是知識在行為的前面發生的。他是說當人在進行道德實踐過程當中,比方說一個人的一念閃動過程當中,同時必須或者說必然也就有良知這個東西也閃動了。同時,良知就會告訴你,什么是對什么是錯。當良知告訴你什么是對什么是錯的時候,你也必然地會響應這個良知的命令,按照這個良知的命令去做事情,這就是陽明學意義上的知行在一個人的意識活動過程當中是一個合一的過程。舉個簡單的例子,我一念閃動,我要隨地吐痰。當這個錯誤的念頭發生的同時,良知告訴我隨地吐痰是不對的,不能做。那么我就把這個行為給克制住了,這就等于致良知。所以陽明的原話是這樣:“一念發動處,便即是知,便即是行”,這句話是非常典型的,非常好的一個案例解答什么叫做知行合一。
(本文轉載自公眾號“紹興文化影視頻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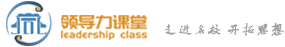
















 加多寶
加多寶 IBM
IBM 摩拜單車
摩拜單車 vivo\oppo
vivo\oppo 中興
中興 GOOGLE
GOOG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