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在1902年的《欽定大學堂章程》(“壬寅學制”)中,即規定商務科修習“商業史學”、仕學館修習“理財學史”等課程。其中“商業史學”接近于今天的經濟史,“理財學史”則更接近于經濟思想史。同年,梁啟超根據Ingram(英)、Cossa(意)和井上辰九郎(日)等人著作撰寫了《生計學學說沿革小史》,這被認為是中國最早研究外國經濟思想史的專門文獻。自此之后,經濟史和經濟思想史的研究與教學一直是中國大學經濟系科的重要組成部分,直至今日仍然大致如此。
之所以說“大致如此”,主要是因為當下國內的經濟史學并不算繁榮。部分重點高校的經濟學院(系)開設了經濟史和經濟思想史類的課程,但多為選修課程。還有很多高校沒有開設相關課程。由學術研究角度觀之,經濟史受到西方主流經濟學影響較大,而經濟思想史特別是中國經濟思想史的研究范式還較為傳統,難以適應日益數理化和量化分析的主流經濟學發展趨勢,導致無論在大學課堂還是學術界對經濟思想史包括經濟史在內的經濟史學重視程度都不夠。
然而事實上,在經濟學領域有重大建樹的學者往往特別強調經濟史學的學習和研究。熊彼特在其多部論著中認為,經濟研究要將經濟理論、歷史和統計結合起來。他尤其看重歷史在經濟分析中的作用:“如果一個人不掌握歷史事實,不具備適當的歷史感或歷史經驗,他就不可能理解任何時代包括當前的經濟現象。”
筆者以為,除前輩學者們的寶貴經驗之外,學習經濟史學尚有如下幾點必要。
第一,有利于樹立“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中國有著綿延幾千年的燦爛文明,歷史底蘊深厚,思想資源豐富。特別是由于古代中國經濟發展水平長期居于世界領先地位,在經濟思想和經濟政策方面有許多首創性的貢獻。例如,公元前2世紀西漢的賈誼明確指出了“奸錢日繁,正錢日亡”的貨幣現象,這要比格雷欣定律描述的“劣幣驅逐良幣”早1000多年。南宋政府對貨幣發行采取“稱提”之制,已經是相當成熟的貨幣調控政策體系。這些經濟史和經濟思想史上的寶貴思想財富,能夠幫助我們正確認識中華傳統文化的地位與貢獻,有利于自覺樹立“四個自信”。
第二,有利于科學評價和借鑒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理論。自1776年亞當·斯密出版《國富論》以來,西方經濟學隨著資本主義的興起日趨復雜化、系統化和數理化,目前在世界范圍內占據了經濟學分析范式的主流位置。西方主流經濟學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科學的?對中國究竟有多大的借鑒意義?一方面需要在實踐中得到印證,另一方面也可以通過經濟史學的分析進行理論上的檢驗。中國漫長而連續的歷史時期和豐富的經濟活動記錄為某些經濟理論提供了自然實驗的機會。這在世界其他文明里是較為少見的。與此同時,經濟史學往往將經濟現象納入更長時段展開研究,某些經濟理論在短期內顯現不出的效果在長期中就會顯露,理論是否科學、普適就有了新的評判標準。
第三,有利于指導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設。“市場經濟”的概念起源于近代歐洲,隨后經日本傳入中國,然而“市場經濟”的內容在中國卻有著更悠久的歷史。《史記·貨殖列傳》里面記載的商業人物和案例,生動反映了兩千多年前中國市場經濟的發達程度。研究經濟史和經濟思想史,在很多方面能夠為當下經濟發展提供智慧啟迪。羅納德·科斯在2011年對此有一段經典評述:“中國有悠久的商業與貿易的歷史,家族企業和集市長期存在。……在其市場轉型期間,中國自然地從傳統中找到了許多相關的理念和制度。隨著對市場經濟的追求,中國反身求己,回歸到自己的文化根源,這個發展令人矚目。”
第四,有利于正確認識新形勢下的對外國際合作交流活動。在中國積極推進“一帶一路”倡議過程中,極少數國家和地區抱有戒心或疑慮。中外經濟史學的研究清晰表明,在持續數千年的絲路貿易中,中國不是唯一的受益國,沿線相關國家和地區都因此得到發展和繁榮。正如克羅地亞經濟部副部長萊韋里奇所說:“絲綢之路是所有國家的寶貴歷史財富,希望這種絲路精神能夠讓我們銘記在過去幾個世紀內的貿易合作。”
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講到,“要重視發展具有重要文化價值和傳承意義的‘絕學’、冷門學科。這些學科看上去同現實距離較遠,但養兵千日、用兵一時,需要時也要拿得出來、用得上”。經濟史學無疑就是這樣的學科。
原文載于《學習時報》2018年4月2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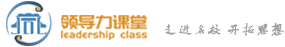




























 加多寶
加多寶 IBM
IBM 摩拜單車
摩拜單車 vivo\oppo
vivo\oppo 中興
中興 GOOGLE
GOOG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