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的輕重術和亞當斯密的《國富論》
管子是齊國的宰相,所以他在治國中要解決很多經濟的問題。管子所處的這個時代,中國春秋的早期,這個時代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特點,正好冶鐵技術上來了,因為鐵器的使用,使得原來沒有辦法對付的樹根可以對付了,農田的面積就可以大大的擴展,農業就發展了,這是管子的時代。

在管子的時代里,就有很重要的經濟的發展,我們今天叫輕重術,輕重術就是掂一個商品。我們經常說貨幣貶值,票子變毛了,我們說東西變貴了,貴重,輕重就是這樣來的。
我們今天通過改革開放這幾十年,中國的經濟高速成長,其中得益于什么呢?就是我們引進了市場經濟。我上大學的時候,大學校園里風靡了一套書,叫《走向未來》叢書,有一本叫《看不見的手》,實際上就是亞當·斯密的《國富論》。
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事關重大。亞當·斯密是英國人,他的《國富論》出版發行于1776年,是歐洲啟蒙運動的前期。我們都知道,歐洲啟蒙運動開創了人類現代化的時代。整個現代的所有思想價值觀,那是從啟蒙運動開始的。在啟蒙運動里,從法國開始的,最后燃遍了整個歐洲,席卷了整個世界。
啟蒙運動干兩件事情,第一,反對宗教神權,張揚人的理性,第二,反對封建王權,宣揚民主與自由精神。法國的啟蒙運動熊熊大火燃起來的時候,里面誕生了一個著名的宣言,叫做《人權與公民權宣言》。
而當法國《人權與公民權宣言》誕生的時候,在美國還沒有思想價值。所以美國人看到以后覺得很不錯,就把人權精神引入到了美國的憲法里面去。
法國人為了向美國表達敬意,就送給了美國那尊自由女神像。我們很多人都見過自由女神像,跟她合過影,但是你內心應有的東西未必當時有。就是當你看到自由女神高擎的火炬,但你看到火炬上熊熊燃燒的圣火的時候,你心中沒有燃起應有的自豪感,為什么呢?因為火炬的圣火是在中國點燃的。
早期的思想家都非常熱愛中國的文化。亞當·斯密畢業于英國的牛津大學,畢業之后他就到了英國的格拉斯哥大學擔任了道德哲學的教授。他在講課的時候,把講課的課堂講義整理出版,就是著名的《道德情操論》。
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操論》是我建議大家一定要讀的,《道德情操論》這本書為亞當·斯密贏得了巨大的社會聲望。以致于有一位英國的公爵,看到這個書以后,就一定要請亞當·斯密做他兒子的家庭教師。
大概是在1763年,他就找到了亞當·斯密,當時亞當·斯密還是英國格拉斯哥大學的教授。他就跟斯密說,請他去擔任公爵兒子,也就是未來繼承公爵爵位的小公爵,給他做家庭教師,兩年半。這兩年半的任務是什么?陪著那個孩子游歷歐洲大陸,主要就是法國,因為那個時候歐洲最重要的國家就是法國。這個時候也正是英吉利海峽兩邊,剛剛結束了長達七年的英法戰爭,實現了和平。
亞當·斯密就面臨著要辭去格拉斯哥大學的教職,而格拉斯哥大學的教職是非常豐厚的報酬,一年150英鎊,那是非常高的。但是這個公爵告訴他,我給你一年300英鎊,比在大學拿到的年薪還要翻了一倍。同時,兩年半以后你就可以退休了,你退休之后愿意做什么做什么,但是我每年都給你300英鎊的退休金,這給亞當·斯密很大的吸引。所以,亞當·斯密最后到大學辭去了教授的職務。
他從英國到法國,大概在1764年年初。他們踏上法國的土地之后,因為英國的公爵是很有身份的,所以他得以能夠見到很多法國重量級的人物,這里面有一批非常重要的學者,就是法國重農主義學派。
法國重農主義學派的開山鼻祖,魁奈,在法王路易十五那是很有地位的,魁奈做他的御用醫生。這個時候,重農主義學派里面的二號人物,叫杜爾閣,是法國的財政大臣,也做過法國的總檢察長,所以,地位都非常高。亞當·斯密到了法國以后,就和重農主義的這些著名人物來往密切。
我們今天看到他的《國富論》,他是1764年到法國以后,才開始動筆寫《國富論》的,《國富論》可以說成為我們經典經濟學的開山之作,也是自由資本主義的開山之作。
我們今天說亞當·斯密是現代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從這本書往上長出來的,還有一本著名的著作叫做馬克思的《資本論》。馬克思對亞當·斯密的評價說,因為亞當·斯密,使得政治經濟學成為了一個獨立的學科,成為了一個完整的學科,評價也是非常高的。
《國富論》有三十多處跟中國有關
我們今天看到的《國富論》里面有三十多處都跟中國有關,都在討論中國的問題。為什么在《國富論》里面,有這么大的比重在說中國的問題呢?是因為亞當·斯密在法國的時候,1763年,法國有兩個中國的留學生,到了1763年底,這兩個中國留學生學期已滿,就面臨著要回國。而杜爾格作為英國的財政大臣,以這樣的身份向英國政府申請挽留這兩位中國留學生,在法國繼續多待一段時間,因為杜爾格有問題,要向這兩個中國留學生來討論。
他寫了52個跟經濟有關的問題,他希望這兩個中國留學生用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替他考慮。他怕這兩個中國留學生不能夠完全了解,所以他在這52個問題之外,寫了很長的解釋性的文字,這52個問題就是著名的《中國問題集》。
而此時,1763年年底到1764年,在這個過程里,亞當·斯密來了,而且跟杜爾格過往甚密。因此我們有理由說,亞當·斯密是見過這兩個中國留學生的。這兩個中國的留學生,一個叫高類思,一個叫楊德望,他們是在那里學神學的。但是,法國人向他們請教經濟學的問題。
杜爾格的《中國問題集》在1766年得以在報上連載,后來變成書出版了。而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是在1766年之后的十年,1776年在英國出版了。亞當·斯密《國富論》出版的那一年,正是美國《獨立宣言》誕生的那一年。所以在大西洋的兩邊,還有這樣的巧合。
當亞當·斯密《國富論》出版的時候,法國人怒了,尤其是重農主義學派的學者怒了,他們說亞當·斯密抄襲了杜爾格的東西。重農主義學派有個重要人物叫奈穆爾,他甚至說凡是抄杜爾格的都是對的,凡是沒抄杜爾格的全是錯的。
重農主義學派是法國思想界非常重要的學派,他們的論文絕不引用希臘人的句子,他們只引用中國圣賢的句子,因為他們熱愛中國,他們不喜歡希臘。不僅如此,他們每年出版的年鑒、論文集,都在上面標上出版印刷地:中國北京。這是十八世紀,重農主義學派對中國是非常的熱愛,以致于他的開山鼻祖魁奈號稱是歐洲的孔子。
而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就是誕生在這樣的環境里,充分地和重農主義學派進行交流。所以我們今天看《國富論》,對重農主義學派的思想是持極大的認同與同情的,而堅決反對重商主義。
關于這一個對比,上海古籍出版社就找到我,向我預約了一個命題作文——對比亞當·斯密與中國的管子,所以我就寫了《管子與亞當·斯密》,在201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了,在這兩個人之間,做了一個跨文化的對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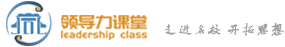







 加多寶
加多寶 IBM
IBM 摩拜單車
摩拜單車 vivo\oppo
vivo\oppo 中興
中興 GOOGLE
GOOG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