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關鍵詞】儒學 現代學科 現代性 中華文明
為什么一代不如一代?
年前與一位學者聊天,他本不是研究中國哲學的,但最近出于興趣看了些中國哲學研究論著,最后得出這樣的結論:一代不如一代。他非常感嘆地說,如今研究中國哲學的人是一代比一代差了,只要拿今日中國哲學界最突出的學者與馮友蘭比一比就知道,沒有一個人在氣象、格局、規模上能與馮先生相提并論,更不要提王國維、熊十力、牟宗三、錢穆等老一代學者了。
這位朋友的感嘆引起了我的沉思,我想這個問題是不是值得探究一下?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呢?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比如當今大陸學者外文功底及西學訓練多半不如老一代,跟馮友蘭、陳寅恪等這樣受過西學嚴格訓練的學者相比有較大差距;又比如當今學者國學基礎多半不如老一代,未經過老一代那樣專門、系統的訓練,更無老一代學者那樣的家學或師承淵源。不過,要是拿王國維、錢穆、熊十力、唐君毅、徐復觀、馬一浮、梁漱溟等人來比較,可以發現這些人的西學功底不見得有明顯優勢。而在國學功底和基礎訓練方面,今日治國學者,要說沒有經過專門、系統的基礎訓練似乎很多人會不服氣。畢竟那些在中國哲學或思想史方面讀到博士畢業的人,在文獻基礎方面也是經過了相當專門的訓練的。
那么問題究竟出在哪里呢?讓我們先從今人治國學的方法與老一代之不同說起。稍加分析即可發現,今日治國學特別是儒學之人,大都分散在大學的哲學、歷史或中文等系科里,其中以哲學系(所)之中國哲學史專業最具規模。在歷史學科有(中國)思想史、(歷史)文獻學等專業也與此相關,其治學方法更重文獻與實證,與哲學學科注重概念分析與抽象思維有所不同。由于歷史、中文等學科在儒學研究方面,迄今為止未成整體氣候(盡管不排除個別人成就斐然),因此我在本文中將重點以哲學學科為對象來分析。[①]從學科體系上看,今日中國的學科體系是完全模仿西方建立的,這一體系不能給國學或傳統經學一個獨立的位置,而是將傳統的經學或國學“五馬分尸”,打散之后分布到文、史、哲等學科中,由此也必然導致治學方式的重大轉變。具體體現在三個方面:
(1)古人治學的第一課是從小將經典反復背誦,背得滾瓜爛熟。經典對他們的影響并不限于內容或思想,而且包括相應的思維方式、價值規范、行為規矩等等。盡管背誦(特別是年幼時)可能并不馬上吃透文義,但是實際產生的影響卻不可低估,可能是極其深遠的。可以說經典在不自覺中滲透到古人的生活中,融解在他們的血液里,構成了他們生命的一部分,使他們從待人接物到人生價值標準,均受到了經典的實質性影響。
(2)古人主張研讀經典一定要結合自己的生活實際來理解,對于一些自己暫時不明白、不理解或消化未透的文句要仔細“熟讀”、反復“玩味”,其最高理想是“自化”、“自得”;因些,要滿懷崇敬之心來讀經典,將經典的含義與自己的生命體驗緊密結合,絕不脫離自己的人生經驗追求所謂純客觀的意義。對經典理解的程度,也取決于或說明了一個人人生境界的高低。經典的含義不是“客觀的”,同樣的文本對不同的人來說含義可能完全不同。
(3)古人主張治學與做人不分:一是通過讀書來修身,確立人生的志向和安身立命之本。修身是一輩子做不完的功課,古代的圣賢在完善人格和性格修養方面的大量教誨正是后代學者們永遠要用心去體驗和實踐的。從先秦儒學到宋明理學,儒家修身傳統源遠流長,代代創新。二是將經典思想應用于當下生活實際中去。因此,對于經典中的重要教導,切不可過目則忘,而是必須在待人接物中嚴格遵守,時刻應用,否則為學的意義就沒有了。
然而,古人在這三個方面的治學方法在今天的學科體系中幾乎已經被完全拋棄。今日治國學則出于學術研究的功利需要,需要撰寫出相關的具有“知識創新”意義上的作品,對經典的理解必須具有高度的“客觀性”,符合嚴格的邏輯論證標準;沒有人要求他們以上述方式來讀經,更不把修身和做人當作治學的首要目標,經典自然也沒有辦法融入他們的實際生活,從而與他們的人生意義相分離。無論是胡適等老一代所謂“資產階級”學者,還是當代的馬克思主義學者,都主張要用“科學的”方法來研究經典。其主要特征是強調要以“客觀的”態度,甚至辯證的、一分為二的方法(馬克思主義者強調)研究,“吸其精華、除其糟粕”;主張不能盲目迷信經典,不能有“主觀的”感情色彩。這種治學方法在過去一直被視為最科學、最先進。而在今日的中國大陸,從事“中國哲學史”、“中國思想史”、“歷史文獻學”等一些學科的人們,雖不再完全遵守這些方法,很多人對經典充滿了同情的理解和情感的認同,但是他們置身于其中的學科體制,卻也決定了他們不需要用古人那種方式來治學,而主要沉浸于知識化的研究、分析和闡述。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臺灣、韓國、日本等儒學曾較為發達的地區。總之,今天學術界的主流意見是認為,經學傳統的中斷理所當然,是一種“時代的進步”,合乎現代化潮流。
如今看來,20世紀以來廢除經學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一代又一代國學研究者人生意義之源被堵塞,安身立命基礎被掏空。在這種情況下,自然出不了大儒或國學大師。為什么這樣說呢?這是因為今天學科體系下盛行的治學方式決定了經典賴以塑造人心靈的方式不再存在,人們對經典的研習與其人生意義的塑造過程相隔離。今天我們看到,原有的儒學或經學話語系統被完全拋棄之后,國學研究者們也未能創造出任何一種新的、代表一個無窮無盡意義的空間、或使人性向永恒升華的話語系統,盡管他們確實仍然可以從經典中學到很多東西,并啟迪自己的人生。畢竟一種具有無盡意義的空間、或可使人性向永恒升華的學問傳統并不多,在中國有儒、道、釋傳統;在西方有希臘以來的人文社會科學傳統、基督教傳統。現代的中國人既然拋棄了過去的國學傳統,在用西方學科范疇研究國學的過程中又扭曲了西方學術的認知主義精神,其不能創立新的、有無窮意義的思想空間是很正常的。其結果就是:今天我們只能看到一些明星式學者,而看不到“大儒”、“大師”。相比之下,馮友蘭、牟宗三等人雖然治學方式上已經有意識地“西化”,但他們畢竟從小飽讀“四書”和儒家經典,他們接受經學或國學訓練的方式仍然是傳統的,所以在安身立命方式上仍然不脫傳統的意義系統。這是他們能成為“大師”的重要原因,但是他們的弟子們就不一樣了,讀書的方法不同了,培養人生意義的源頭也發生了改變,造成了沒有前人那樣博大的胸襟、宏闊的氣象和巨大的規模。
然而,我在這里絲毫不是想詆毀從哲學、歷史等現代學科的視野出發來研究儒學,也不是說這種類型的研究一定不能取得巨大成就都,事實上應用這類研究方法研究儒學而取得較大成就的人無論在中國還是在國外都不少,但是從整體上看這類研究方式本身注定了儒學傳統中斷的命運。我們必須認識到,現代西方學科體系本來不是為培養儒家式的精神傳統而存在的,它的內在旨趣、邏輯范疇、研究方式均與儒家傳統存在本質上的不同。盡管這些學科進入中國后也在不知不覺中被嚴重的“中國化”了,帶上了“中國特色”,但是這些在中國已經“變形”的學科,仍與儒家傳統代表兩套不同的話語方式。這決定了傳統儒學或國學的意義基礎在現代大學里無立足之地,現當代中國哲學工作者不可能成為國學大師乃勢所必然。也許從哲學、歷史等現代學科的角度來研究儒學或國學將在中國或國外永遠持續下去,也許這些學科存在的合法性不成問題,但是問題在于:無論是在西方還是中國,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儒學曾經盛行的東亞其他國家或地區,今天人們紛紛認為:只有從這類學科的角度來研究儒學才“合乎時代潮流”,才是“科學的”,于是用這些現代學科的方式來研究儒學或國學者成為時髦。
有人問我:“儒學的現代意義何在?”
我反問他:設想在今天的世界上不允許存在基督教教堂,基督教教義只能在大學文、史、哲等學科體系中被作為知識的對象加以研究和講解,那么基督教還能作為一種活生生的傳統存在下去嗎?答案是什么一目了然。顯然,人們并不認為基督教教義只有按照科學的方式來研究才合乎“時代潮流”,而在大學宗教學系或神學院之外,還必須存在教堂,才能確保該宗教作為一種活的傳統存在下去,其原因正在于:這個世界上并不是任何精神價值傳統都必須納入到現代學科體系中去、作為“科學研究”對象的;尤其是那些宗教性質的精神傳統,是不能被完全納入到以知識生產為主要目的的文史哲等學科中去的。因為二者代表兩套完全不同的話語體系。如果一切惟“科學”是從,或者用現代學科的知識生產邏輯來代替人類的精神價值傳統,后果只能是人類許多古代偉大傳統的人為中斷。這一結論對于儒學傳統來說也完全適用。因為雖然儒家算不算宗教仍有爭議,但是目前西方學術界多認同儒學帶有典型的宗教性,我認為儒學帶有典型的宗教性是無庸置疑的。[②]事實上,我們仔細比較中國古代儒家的話語系統,可以發現其精神旨趣、邏輯構造以及上述三個方面的治學方式均與西方人文社會科學迥然不同,而與基督教等宗教傳統更加接近。由此我們可以發現將儒學納入到現代學科體系中去的悲劇是什么了。事實上,古人治學的體制空間如書院、塾堂、書堂之類被正規的、高度西方化的學校體系代替,就相當于用大學來代替教堂。
回歸原有的話語系統是儒學存活的首要前提
重思20世紀以來儒學所走過的道路,可以說走的是一條自掘墳墓、自毀家前程的歧路。尤其是前述的儒學大師如馮友蘭、牟宗三、唐君毅等人,可能沒有意識到他們所開創的中國哲學道路,非但不能接續儒家傳統,而且實際上使儒學或國學傳統走到了一條與其初衷完全相背的道路上去。
那么,為什么在現代的中國或東亞,儒學會走上上述這樣一條道路呢?為什么現代中國人如此地崇拜和迷信西方學科,心甘情愿地放棄自己固有的話語系統呢?根本原因在于:在西方文明的強大勢力下,對于儒學的現代意義失去了信心。要理解這一點,需要從儒學這門學問的特點來看。在這一點上,儒家與基督教、佛教等其他宗教又有所不同。我們知道,儒家傳統與人類其他許多宗教的一個最大不同,就是它的“此岸性”,儒學不將人生的希望寄托于天國或彼岸,而是建立于世俗人間。儒家強烈的“此岸性”,導致他們要全面安排人間世界的秩序,并告訴人們此岸的“天堂”在哪里。這一特點決定了儒家不得不面對現代西方文明的強大沖擊。因為現代西方文明向人們呈現的是古典儒家所從未想到過的新型社會,其中很多看來是進步、文明的因素在儒學的理想王國里根本不存在,也是儒學連想都不曾想到過的。在這一強烈的沖擊下,很多中國人喪失了文化自信,對儒家所構造的理想王國產生了厭棄心理;而那些從小接受儒家傳統熏陶、對儒學的核心價值愛不釋手的儒者們,不得不費盡心機試圖將儒學現代化,結果用西方現代學科來整理國學就成為一種似乎是“在中學與西學之間架橋”的發明,一種可使國學“現代化”的創造。
由此我們發現,20世紀儒學之所以深陷學科的泥潭、丟棄了固有的話語系統,其深層原因是懷抱“為生民立命”理想的現代儒家,處理不好儒學與現代性的關系。所以我們看到,現代儒學誤入歧途的另一個重要標志就是,儒學從一種“進德修業之學”演變成一種與其自身傳統完全相悖的“知識之學”。以牟宗三等人為代表的進步的儒家學者,以無窮探索的精神和堅忍不拔的意志研究現代性的根源,試圖厘清儒學的現代功能,他們雖然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不僅所取得的成就非常有限,而且對后來的讀書人產生了巨大的誤導效應。具體來說,當儒者不再把主要功夫放在修身和進德之上,他就放棄了自身固有的話語系統,走到了“有放心而不知求”的地步,步入了宋明新儒家所一再反對的、追逐“聞見之知”的歧途,怎么可能不導致意義的喪失和學統的中斷呢?
然而,我的意思并不是說儒學不需要處理自身與現代性的關系,或者反對從事知識化的論證。我們都知道漢代的經學、清代的乾嘉學派,都以考據和訓詁見長,用余英時先生的話說,充滿了“智識主義”的特點;畢竟儒家不僅“尊德性”,而且“道問學”。[③]但是問題在于,漢代和清代的“智識主義”(intellectualism今天較流行的譯法是“認知主義”),與20世紀儒學智識主義有兩個根本性的差異,正是這兩個根本性差異,導致20世紀儒學智識主義的后果是災難性的,而前者則不然:
①古代的智識主義是在中華文明的原有理想和框架沒有發生根本動搖的情況下興起的,因此嚴格說來他們所追求的并不是如余英時所說的純粹的“智識主義”,而是如何更好地實現儒家固有的文明理念。而智識主義那種為知識而知識的理想在漢學中并不存在,清代漢學背后起支撐作用的恰恰是一個異常堅固的中華文明理想。
②古代的考據家們并沒有放棄儒家應有的治學傳統和話語系統,包括前面所說的三個方面的治學方法。漢學家們并沒有把經學系統割裂、打散,“五馬分尸”,從而不可能導致經學原有的意義系統被破壞。對于他們來說,讀書和治學,顯然對個人來說是為了成圣成賢,而對社會來說是為了治國平天下。
基于上述兩個原因,古代的儒學“智識主義”(如果存在過的話)可以從兩方面來強化儒家原有的信念:一是他們對中華文明作為一種具有永恒意義的空間和精神圣殿的信念,這一信念可以通過訓詁和考據圣賢經典而得到加強;二是將經學思想應用于自己的當下生活,在待人接物和人倫日用之間獲得豐富的人生體驗,并感受自己人生安身立命的基礎。考據家、漢學家當然個個都是衛道士,是堅定不移的儒家傳統捍衛者。所以其“道問學”并不以拋棄“尊德性”為前提,甚至可以說是以新的方式使二者協調起來、相互促進、共同發展。
相比之下,現代新儒家則是在中華文明的理想幾近徹底崩潰的悲慘處境下開始探討儒學與現代性的關系。在這種情況下,由于一些基礎性或前提性的問題不清楚,整個儒學話語系統的合法性都被打上了大大的問號。由于將儒學等同于哲學,于是不自覺地用西方哲學的知識話語來代替儒學自身原有的修養話語;由于西方現代性的強勢影響,人們開始用西方學科體系代替原有的國學體系,并主張廢除經學;由于對科學力量的無限崇拜,人們開始用科學精神取代“尊德性”精神。就這樣逐漸走上了一條儒學原有的話語系統被埋葬、儒家固有的意義世界被毀滅的道路。現代新儒學智識主義的這一致命缺陷之所以會產生,是由于他們接觸西方文明時間不長,對于西方現代性的發生根源缺乏深刻、全面的了解,同時由于他們缺乏現代社會科學研究工具,他們的研究方式可以說是不中不西、不倫不類。以牟宗三、唐君毅、馮友蘭等現代新儒者只能從傳統儒學特別是宋明理學的心性范疇出發來解釋現代性(特別是科學與民主),并試圖以儒家境界論作為衡量現代性的標準,其失敗幾乎是從一開始就注定了的。我們看到,一批現代儒者們幾乎將畢生精力用之于從事儒學本來并不擅長、也不符合儒學傳統特征的理論論證,結果卻收效甚微,其中最典型的莫過于牟宗三、唐君毅等人。其他一些學者如熊十力、馬一浮、錢穆等人未在解釋現代性方面花足夠工夫,他們的學問也就相應地使很多學者感到沒有現代意義,似乎“過時”了。
今天我們認識到,西方現代性特別是民主、科學發生的根源,其實不是象現代新儒家學者所理解的那樣,來源于某種“主體性結構”或哲學思維方式,即牟宗三所謂“分解的盡理之精神”或“理性之架構表現”,而是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的產物。從某種程度上說,它們的出現有相當大的偶然性。具體來說,民主的出現,乃是人類社會伴隨著商業的興起沖破了血緣關系紐帶、出現了市民社會及公共領域情況下的特定產物;民主并不是什么可以超越一切客觀的歷史條件普遍有效的理想的社會制度。現代大國的民主政治以個人主義為基礎,以長久的底層市鎮生活實踐為前提,要求比較高的公民素質,等等。而科學的發生,也不是如一些現當代中國學者所理解的那樣,來源于追求功利效果和征服自然的精神,而是來源于希臘有閑階層的“求知欲”。希臘人的“愛智慧”,愛的是一種非功利的思辨精神,而這種精神對于人性的價值就是思想的解放、視野的開闊、知識的增長等等。這種非功利的求知欲,是人性普遍具有的,但是成為一種專門學問而蔚為大觀,則與古希臘特定的社會政治環境為之提供了充分發育的溫床有關。中國古代社會形態與古希臘不同,沒有出現現代意義上的“科學”是完全正常的。這就是說,無論是民主、還是科學,其未發生在中國,都與儒學的主體性結構或哲學思維方式等關系不大。儒學也不必因為中國沒有開出民主、科學而自慚形穢,更無需亡羊補牢,重建一種新型的、能夠開出民主和科學的儒學來。[④]從境界論的角度講,我們也可以發現,科學、民主的精神境界與儒家的精神境界性質迥然不同,不具有可比性,就象我們不能拿物理學與基督教比較何者境界高一樣。牟宗三、唐君毅等人以儒家境界論來衡量現代性,潛含著用儒家價值作為衡量一切人類活動的標準的錯誤傾向,正確的方式是從儒家價值傳統中找到有益于現代性向正面發展的資源,而不是無限地拔高儒學,仿佛儒學可以包括一切、開出一切。
進一步來看,如果認識到中國古代社會的一系列成份,包括曾經出現過的井田制、郡縣制、封建制、君主制等等,也并不是儒家傳統所“開出來”的,那么我們就可以達成這樣的認識:儒家的“此岸性”并不意味著它必須能開出某種特定的制度、社會形態或思想傳統,而在于它能在具體的社會歷史背景下幫助人們尋找人生的意義和文明的理想。因此,儒學的現代意義不在于它能否開出現代性,而在于它能針對現代性在政治、經濟、制度等一系列方面所給人類提出的新挑戰,幫助人們從困境中走出來,達到理想的歸宿。回到了這樣的起點,我們也就認識到:現代儒學沒有必要將那么多工夫白費在從事思辨性的理論論證上(這本來不是儒學的特長,而是西方人文、社會科學的特長),而應將主要工夫用之于:面對民主、自由、法治、科學這些新鮮事物的挑戰,如何尋找生命的意義和重建文明的理想。而所謂的重建,也只是從儒學的價值傳統出發,來看看能不能找到真正對現代人有益的資源。在這一過程中,儒學決不能也沒必要放棄自身原有的話語系統,而是從其固有的話語系統出發,來回答現代性所帶來的新問題。比如在尋找生命的意義方面,儒家修身傳統并未過時,我們今天完全可以從先秦儒家特別是宋明新儒家的修身傳統出發,從中找到對于診治現代人的精神疾病和心理健康問題的有益良方。[⑤]在這方面,只有現代儒家能用自己切身的修身體驗來說服人們,達到治病救人的成效,儒學的現代意義才會再次呈現,因而一切取決于能不能出現這樣的現代新儒家。遺憾的是以馮友蘭、熊十力、牟宗三等人為代表的現代新儒家在這方面恰恰用力不多。
這里必須一再強調的是:我在這里絲毫不是認為,現代學科體系及西方現代性與儒家傳統之間本質上就是對立的、你死我活的關系。恰恰相反,我完全同意狄百瑞、杜維明等人的有關觀點[⑥],那就是儒學可以在多方面對現代性構成支持,它與西方的自由主義精神、市民社會傳統及民主、法治等制度都可能相互支持,甚至有比后者更積極的意義。我在這里所主張的是,儒家傳統的獨立性不應由于現代性的到來,以及現代學科體系的建立而被取代。就象我們不能因為崇拜現代科學的威力,而認為神學或宗教思想只能在大學里、作為文史哲等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對象而存在,并從而主張取消教堂-神父-牧師制度一樣。因為儒學有自己的話語系統、學理邏輯及其治學方法,有其自身的獨立性和完整性;一旦將經學體系切割、分散,它原有的話語系統就無法保存;一旦將其千百年來在實踐中形成的治學方法拋棄,儒家自身的意義世界也就被連根拔起。如此下去,儒學傳統的人為中斷就勢所必然,更不要指望靠現代學科體系來培養出國學大師或“大儒”來。
綜上所述,似可得出這樣的結論:20世紀儒學所走過的彎路,主要由于未能正確定位兩個關系,即(1)儒學與西方現代學科體系的關系,(2)儒學與現代性的關系。未能正確定位這兩個關系的結果,是儒學丟棄了自身固有的話語系統和意義世界,使后來者精神世界被掏空,喪失了安身立命之本。搞清了這一點,我們也就明白了今天儒學復興的首要前提。那就是,儒學必須從現有的學科體系中走出來,回歸原來的話語系統,并在這一基礎上重建自身的意義世界,否則儒家傳統就不可能存活。而要做到這一點,回歸經學是其中之一,接續歷史上的修身傳統則是另一個重要方面。未來的儒學可以借用現代人文社會科學的成果和方法,但是從整體上必須與現代學科體系劃清界限,而不能將自身消融在文、史、哲等現代學科之中。對于現代性問題,儒學思考它的方式也必須轉變,那就是,不是從源頭上尋找中國未出現現代性的根源,而是思考:在現代性已經勢不可擋的歷史條件下,儒學如何從自身固有的資源出發來應對它的挑戰,為現代人重新尋找精神的家園,為重鑄人類文明的偉大理想而奮斗。搞清了這兩點,儒學的現代發展才算走上了正常軌道。
未來中華文明的基本框架:夷夏之辨與王霸之辨
我們說過,儒學的根本特點之一是全面規劃此世(this-world)生活,在此岸而非彼岸建立“天堂”。這決定了今天中國儒學面臨的任務并不僅僅是修身養性這么簡單,而是仍然必須從根本上承擔起指導中華文明前進方向的任務,確立起中國文化的最高理想,還必須為今日中華文明的重建提供基本框架。因為今日中國儒家在人間建立“天堂”的第一步,就是對未來中華文明的形態作出全面的說明。對于中國人來說,這個問題未解決,導致一個多世紀以來知識分子在精神上彷徨四顧、流離失所,無數中華兒女喪失了對中華文明的信心。而對于儒者自身來說,這個問題不解決,則意味著安身立命之本被連根拔起,這正是梁漱溟、熊十力、馮友蘭、張君勱、牟宗三、唐君毅、徐復觀等人以來的哲人們整日焦慮難安、費盡心力探討現代性的根本原因。而既然如前所述,儒學與現代性的關系,不是從理論上說明儒家如何“開出”現代性,而是指思考儒家傳統中有哪些有利的資源,可以促進現代性的正面發展,下面就讓我們從這個方面來說明儒學與未來中華文明的關系。
首先,儒學中一個最具生命力的、可能對未來中華文明乃至全球文明自身發展有積極意義的理念是“夷夏之辨”。“夷夏之辨”的精神實質是“文明”與“野蠻”的對立。由于過去的歷史上中國人受地域視野的限制和一些人片面的解釋,有人錯誤地將“中國”等于“文明”,將中國之外等同于“野蠻”,造成了“夷夏之辨”被誤解為一種“中國文化中心論”或中華民族的“種族中心主義”。其實,《春秋公羊傳》中已經充分表述了這樣的思想,儒家衡量“夏”與“夷”的標準不是地域或種族身分,而是其行為是文明的還是野蠻的,即“中國而用夷狄則夷狄之,夷狄而用中國則中國之”。[⑦]讓我們這樣來表述,“夷夏之辨”的現代意義就是,不同文明之間的競爭是文明與野蠻的競爭,只有真正文明的文化或社會才會如百川歸海一樣,真正贏得人類其他文化的尊敬,引起全人類的向往;未來中華文明發展的最高目標決不是追求成為一個新的超級大國,成為經濟、軍事或政治意義上的富國或強國,而是建立一個真正文明、進步的國家,其最高文化理想則是每一個人潛能、創造力與個性的發揮,人格尊嚴與正當自由的確保,以及人生幸福與價值的實現。我們應該讓我們在子孫后代在這個方面與其他人類文明比賽、競爭,才是符合中華文明走向進步的惟一正確道路。我曾在有關文章中提出,今日中國人一定要有古典儒家那種包容宇宙、吞吐六合的胸懷,有“為萬世立法”、“為萬世開太平”的氣概,一定要用真正進步的而不是狹隘民族主義的文化理念引領中華文明走上一條健康發展的大道,要有使中華文明因其文明和進步而成為世界其他文明學習的樣板、變成其他文化紛紛仿效的榜樣和促進人類不斷進步的風范的宏圖大略,使之不僅能成為每一個有教養的中國人的精神圣殿,而且成為世界上一切愛好和平進步的人的精神家園。今日之中國,離這樣的理想還相差甚遠,但是只有樹立這樣的理想,才能為中華民族的長治久安開創永久基業,才能使中華文明在世界民族之林永遠立于不敗之地。[⑧]這樣的思想,孟子早在兩千多年前、在當時的時代條件下是這樣表述的:
孟子曰:“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賈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孟子·梁惠王》)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孟子·公孫丑》)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杰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愿立于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愿藏于其市矣。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愿耕于其野矣。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愿為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于天下。無敵于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公孫丑》)
今天的中國受到來自世界各國特別是西方大國甚至東亞一些國家的媒體的批評多矣。這些批評有的是有關于中國缺乏人權與民主的,有的是有關中國人性格和習慣不好的,有的是有關中國官場腐敗和行政系統,有的是有關公共秩序和社會風氣的……其中誤會和偏見固然不少,但是另一方面也證明我們的國家、我們的社會、我們的文化還離文明、進步的理想相差甚遠。如果我們真的相信孔子“德之流行,速于置郵而傳命”(《孟子·公孫丑》),以及有孟子“仁者無敵”(《孟子·梁惠王》)的信念,那么,“夷夏之辨”正是促進中國全面反省自己社會的問題,并從根本上改造我們的國家,使之逐步走向進步和文明的、儒家式文化原則。
其次,儒學中另一個極富生命力的思想就是“王霸之辨”。不少學者研究指出[⑨],儒家的王道思想可直接引伸為主張行業的自治與理性化,包括學術自治、宗教自治、家族自治、地方自治等等,還包括政統服從道統的特征。我們相信,儒家的王霸思想,對我們理解中國現代性建設的方向,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用今天的話來說,可以說:行業的自治與理性化,同樣是每一個現代人“盡性”的必然要求。因為只有尊重行業自身的邏輯,才符合人性發展的內在需要;只有人們在行業傳統中安身立命,即感受到職業的神圣感與尊嚴;只有行業規則不遭外力人為破壞,才有可能符合人的天性,讓人性的價值得到充分實現。因此,今天的中國各行各業都存在著“正名”的需要,即鑄造行業傳統,實現行業的自治和理性化發展,讓行業從業人員感受職業的神圣感與尊嚴。
必須指出,孟子的王道理想是其性善論的自然延伸。性善論強調“盡心”、“知性”、“養性”、“事天”這一過程,它的精神實質是相信人性的自主能力,并以人性的自我實現為目的。性善論之所以反對霸道,是因為霸道不相信人性有自主能力,霸道假定了人需要靠某種外在的權威和力量才能成全自身,把人拖進一個由外在力量強加的框架。而所謂“仁政”,并不是如現代人所誤解的那樣、強調國君要對人民“施恩”,而是強調發揮人的內在本性,讓每個人的自主性真正調動起來。[⑩]
孟子性善論的必然結論是尊重行業傳統的獨立性,與行業的自治與理性化完全一致,原因有二:一方面,就每個行業而言,只有尊重行業自身的邏輯,才能讓人們實現自身的潛力,才能最大限度的讓人們“盡性”。 另一方面,從性善論的基本精神出發,可以自然引伸出這樣的信念:只要各行各業的人們均能在其行業中“盡性”,即可達致“天下大同”。也就是說,我們不必擔心行業的自治與理性化發展會導致“天下大亂”,只要尊重行業邏輯和社會自身的規律,即可實現天下大治。極權和專制在這里找不到藉口。這說明:行業的自治與理性化,以及捍衛職業的神圣感與尊嚴,是符合儒家傳統的根本精神的,也讓我們對儒家傳統的現代意義有更新的認識。
今天的中國最緊迫的任務是什么呢?我想在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意識形態高于一切、抽象名詞統治百業的價值混亂之后,中國目前最急需要做的事情之一,莫過于重建行業的自治與理性化。行業自治與理性化的重建,也同時是無數人在本行業安身立命之本的建設,人們可以從職業的神圣感和尊嚴中找到自身價值的落腳點。應該認識到,今日中國社會人心混亂、浮躁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人們不知如何在職業行為中尋找人生價值的正確定位,人們從小被教育為一些抽象的名詞和象征符號(如國家、民族、人民、正義、真理等等)而奮斗,而不知道怎樣把自己塑造成為人,特別是怎樣在具體的職業行為中找到個人的神圣感和人性的尊嚴。
今天,我們生活在一個分工高度發達、職業分化日益精細的時代,人們如何在自己的職業中找到安身立命之本關系著其一生的幸福和命運,因為每個人都是特定行業的從業人員,而他們人生價值的一大部分來自于專業的選擇、職業的追求。從這個角度說,如果人們不懂得“盡其性”,即事業的追求不能朝著使自身人性得到充分、全面發展的方向,可以說是一生最大的悲劇。換言之,朝著盡其性的方向來發展自己的事業,做自己喜歡的事,充分發揮自己的潛力,一個最重要的標志就是對職業神圣感和個人尊嚴的體認;這一方向的必然結果就是行業的自治和理性化。所謂行業的自治與理性化,在本文中包括行業傳統的獨立,專業行為自身不受專業之外價值的支配,以及職業的神圣感與尊嚴等。
今天,有責任感、有良知的中國人需要思考的一個重要問題是:未來的中國也許能成為一個世界強國;但是成為強國,并不等于成為一個真正文明、進步的國家。成為一個真正文明、進步的現代國家的基本前提就是,行業傳統空前發達,行業的自治和理性化得以確立;我們不僅有“領導”和“官員”,更有一大批杰出的政治家、教育家、企業家、法官……;我們不僅有經濟的騰飛、政治的進步和科技的發達,更有尊嚴的保障,個性的展示與潛力的發揮,以及人格的全面發展……而這一切,難道不需要以行業的自治與理性化為前提嗎?
第三、中華文明的形態問題。以狄百瑞、杜維明、安樂哲等人為代表的一些現代儒家學者都傾向于從社群主義的角度來理解儒家的現代意義。[11]我認為,一方面,我們要認識到,未來世界的“大同”理想并不體現為各種不同文化的“趨同”(homogenization),文化的多元化(pluralization)即人類文明的多極化發展是惟一可以接受的正確方式。此即《周易·系辭》“天下同歸而殊涂,一致而百慮”,以及孔子等人所謂的“和而不同”(《論語·子路》);另一方面,各個文化又可以以自己的特殊路徑為人類大同作出自己獨特的貢獻。因為每個文化的路徑各有短長,因而可以互補共存,相互學習。從這個角度說,我們可以說,中國的現代性走的將是一條“非形式主義”的道路。所謂非形式主義,指反對形式化的、非人情化的(impersonal)“規則至上”,認為真正適合于中國文化的東西是一種介于規則與人情之間的“傳統”。“傳統”是由一群人在一起形成的某種類似習慣、風俗之類的東西,它不象法律一樣過份注重形式,但通過人心的力量對每個人構成約束。這不是說中國現代性不需要法治,而是說中國現代性的方向之一可能體現在行業的自治與理性化。
民主、自由、人權、法治……這些概念多年來一直被看成為衡量現代性的價值標準。無庸置疑的是,這些概念,以及自由主義,確實能夠維護社會自治、促進行業的理性化。因為自由主義的信念之一,就是把對個人作為社會行為者(社會學中習稱為agent/agency)——無論是作家、學者、教授還是工匠、商人……——即各行各業的從業人員——自身作為目的,而不是單純作為完成其他目的的手段的人格的基本尊重。但是,正如我們在前面已經指出過的,自由主義的局限性在于:它可能導致權利的被濫用;在東方文化中,由于沒有根深蒂固的個人主義傳統,個人自由的絕對化往往導致族群的沖突、人心的撕裂甚至社會的失序等問題。所以,我寧愿選擇用儒家的術語——“王道”與“霸道” ——來表述我們的觀念,我們發現:其實儒家的王道思想在今天可以解讀為“行業的自治與理性化”,它與西方的自由主義也許可以達成“殊途同歸”的效果。
按照狄百瑞的說法,儒家禮學以互助、關愛、理解為倫理精神之核心,而不是一味強調權利。這是儒家傳統中與西方自由主義所不同的東西,也正是這種區別,在狄百瑞看來最難能可貴,因為這種社群主義精神既吸收了自由主義的優點,又超越了自由主義的不足。他認為,禮制類似于西方歷史上的personalism,與individualism不同的是,它表達了對人的價值和尊嚴的尊重,以及對人格全面發展的追求,但認為這些并不是通過訴諸孤立的個人權利和自由來達到,而是在特定的文化傳統和各自的社會共同體及其自然環境中實現的,所以才有益于社群主義。[12]
需要指出的是,中華文明形態的獨特性,和前面所談中國文化追求引領人類文明進步的方向、成為人類其他文化學習的風范和榜樣這兩者之間未必相互矛盾,前者是就事實層面立論,后者則是從規范層面立論。以《周易·系辭》“天下同歸而殊涂,一致而百慮”之說來理解不同文化的道路,既承認不同文化道路的異,也認為不同文化、文明之間有默契、共通之處。文化道路之異是事實、現實,而文化理想、文化理念上之默契、共通是價值、追求。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未來中華文明的基本框架至少可以從三個方面來概括:
一是從“夷夏之辨”即文明與野蠻的區分出發,確立中國文化的最高理想在于每一個人潛能、創造力與個性的發揮,人格尊嚴與正當自由的確保,以及人生幸福與價值的實現。未來中華文明自信賴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和長治久安的萬年大計并非成為一個強國或超級大國,而在于追求以其社會生活的文明、進步程度引領人類文化的進步,成為其他文化紛紛效仿的模樣。
二是“王霸之辨”出發,認識到行業的自治與理性化是未來中國社會發展的基本方向。行業的自治與理性化意味著社會自治傳統的確立,政治不是凌駕于社會之上、可隨意干預社會和司法的太上皇,而是以尊重社會自治和行業傳統為其基本原則;還意味著政治、經濟、商業、學術、宗教、法律、制度等各個領域由賢能來主導,并通過鑄造行業傳統來規范人們的行為。
三是中華文明的形態,是一種以追求相互理解、相互溝通、相互尊重的社群主義生活為特點的社會形態。它是一個尊重個人自由和尊嚴,但不由自由主義和形式主義來統治的社會;其基本社會價值將不是個人自由和權利等,而是仁、義、禮、智、信等。
這些是本人迄今為止所能看到的未來中華文明的基本框架內容。
儒學復興的希望在哪里?
我深信,儒學要復興,就要從全球文化的高度來反思未來中華文明的自我定位、中華文明的方向、中國文化的最高理想以及與此相應的儒學的定位。正因為儒學的高度入世性格,要求今日儒者拿出史無前例的胸襟和氣度來包容整個世界,尤其要從世界不同文化、不同區域的關系的廣闊視野出發來定位儒學的前途,只有對人類文明未來的方向有了相當清楚的認知才能正確理解中華文明的位置和方向。
令人遺憾的是,我們看到今天的許多儒學研究者對世界各民族的文明缺乏同情的關懷,對西方文明的內在活力缺乏應有的理解,整日怨天尤人,抱怨中國文化未受西方人尊重,學術研究也不自覺地陷入于論證中國文化傳統多么“偉大”之上,使其學術研究淪為為狹隘民族主義服務的工具,其根源則是內心世界缺乏精神的支柱和信仰,而對于未來中華文明的方向和目標根本沒有信念,所以只能在功利主義、實用主義和民族主義中自說自話、自我陶醉和自我安慰。這樣一種自欺欺人的心態,來源于他們對于儒家經典的錯誤閱讀方式。
根據本文前面幾部分的討論,我認為今日中國儒學復興的道路可分三步走:
一是打掃戰場、清理外圍。即分辨清楚20世紀以來中國學者在儒學與現代學科體系的關系,以及儒學與現代性的關系上所犯的種種錯誤,從一百多年來的迷途中回歸正道,具體說來就回歸儒家自身的話語系統;
二是確立中華文明未來的基本框架。這包括至少三個方面的基本工作,其一是確立中國文化的最高理想,其二是認清未來中國社會的基本方向特別是行業的自治理性化,其三是厘清未來中國現代性的基本特征,或者說未來中華文明的形態。
三是通過回歸經學和復活修身傳統,培養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現代儒者。
儒學的復興寄望于出現千萬個“真儒”即現代儒家,其特點是自身的生活和生命來踐履儒家的價值,并教書育人,培育一代又一代后來者。他們的人多了,儒學的傳統自然就活了;他們的人多了,所謂的書院重建、現行教育體系改革等等自然也就不成問題了;他們的人多了,我們自然不必擔心所謂的“傳統的現代化”問題了,也認識到所謂儒學體系建構、儒教國教化方案或上行/下行路線等等都會水到渠成,而不必在今日時機未成熟之時操之過急。而所有這一切,前提是必須恢復儒家自身的話語系統和傳承方式。一個真正的儒者必須認識到:在今天這樣一個資訊極其發達,社會自主性空前加強,人們的自覺意識無比強烈的時代,一種真正對于診治現代人的心靈有益的精神價值,必然會吸引無數人的目光,一定能得到全社會的擁護。問題主要出在今天有沒有這樣的儒者,能符合當代人習慣的、最生動活潑的語言來表達儒家的做人智慧,讓成千上萬的人感受到儒家傳統鮮活的生命力。
我曾在有關文章中指出,在過去的歷史上,儒學之所以能永葆青春的活力,是因為不同時代、不同地域的人們總是能從它的源頭出發,找到對于社會方向、文明未來、人性進步、人生歸宿以及文化價值等的豐富啟迪。歷史上如此,今天何嘗不是。因而,今天我們研究儒學,決不是為了“復古”,而需要從儒家的精神傳統出發,分析今天這個時代一系列根本性問題的癥結,告訴人們希望在何方,在荒涼的精神世界中發現精神、道德與信仰的種子,讓流浪已久的靈魂回歸家園。只有當今天的儒家學者能回答我們時代的一系列重大課題,給中華民族指明一條通向進步的康莊大道,讓中華兒女重新找回安身立命之本,為中華文明開辟波瀾壯闊的事業前程,儒學的復興才不會是一句空話。
儒學能不能復興,不取決于我們把它人為地拔高,而取決于我們能從傳統儒學資源中發掘出多少鮮活的思想,對于理解今日中國的出路真正有啟發意義;還取決于通過讀經典,對于我們思考中國現代性問題能激發出多少意義深遠的思想靈感。我們不應當把儒學特別是自己研究儒學的身份當成一群人競爭社會資源和個人地位的資本,在這一潛在思想的驅動下人為地拔高儒學。今天,空談如何改造儒學,來適應現代社會需要,往往流于形式,變成一部分學者體系建構的個人嗜好,反而可能傷害到儒學的現代發展之路。因為儒家傳統能不能被“激活”,依賴于我們在深入體會和理解經典的過程中,對于理解中國現代性能獲得什么樣的新的啟迪。
我們看到,如果我們對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儒學所走過的彎路缺乏足夠清醒的認識,空談所謂儒學復興的任何方案,都可能流行形式和空談。因為問題在于,時代不同了,儒學的智慧和傳統如何能結合今日之需要而被激活,如何讓儒學在現代人特別是普通人的生活中make sense的問題。多年以前,一位美國馬克思主義者告訴我,毛澤東作為馬克思主義者的最大貢獻之一在于能用非常現代、非常中國的語言來“說”馬克思,這才是把馬克思主義經典激活的最重要之道,也是發展馬克思主義的最有效途徑。此條也適用于儒家傳統的復活。
我們還應當認清,儒學的復活,對于站在內部說話的人來說,與站在外部說話的人是完全不一樣的。站在外部說話,說來說去,總難找到信心。從客觀的眼光來看問題,都難免從外部社會效應上來說事。而且對于深受進化論世界觀影響的現代中國人來說,一扯上現代化,就覺得儒家傳統不可能大行其道了;一想到民主、科學,就容易覺得儒家過時了。但對于真正的儒者來說,情形就完全不同,因為他們在親身的生命歷程中體驗到了儒家的精神,他們活生生的生命本身就是儒家現代意義的最好見證。他們能造就自身,也自然有信心造就出新的儒者來,同時也自然對儒學的未來意義有足夠信心。
再回頭談一下儒學的現代意義問題。大體來說,我認為至少有三個方面
一是文化功能:確立中國文化的最高理想;
二是社會功能:(1)促進行業的自治與理性化;(2)以其文化精英主義精神與現代社會的大眾化、庸俗化、功利化、膚淺化作斗爭。
三是個人功能:修身,診治當代人疲憊的心靈。
除此之外,當代儒學若能復興,還能對當代人的家庭生活、道德教育、社會風氣改善等等發生強大的促進作用。但是這些作用需要在儒家正式傳統恢復以后才能逐步顯現。
參考文獻
De Bary, Wm. Theodore,Asian Values and Huamn Rights: A Confucian Communitarian Perspectiv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ombrideg, Massachusetts,London, Engliand, 1998(中譯本參《亞洲價值與人權:從儒學社群主義立論》,陳立勝譯,臺北縣:正中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版)。
de Bary,Wm. Theodore &Tu Weiming(eds.), Confucianism and Human Rights, 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Hall, David L. & Roger T. Ames, The Democracy of the Dead: Dewey, Confucius, and the Hope for the Democracy in China, Chicago and Lasalle, Illinois: Open Court, 1999.
Taylor, Rodney L., The Religious Dimensions of Confucianism, Albany :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0
Tu Wei-ming(ed.),Confucian Traditions in East Asian Modernity: Moral Education and Economic Culture in Japan and the Four Mini-Dragons,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Tu Weiming, “Implications of the Rise of ‘Confucian’ East Asia, ” In: Daedalus: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Winter 2000: “Multiple Modernities”, Vol. 129, No.1, pp.195-218;
Tu Wei-ming,Centrality and commonality : an essay on Confucian religiousness,A revised and enlarged edition of Centrality and commonality,an essay on Chung-yung, Albany, N.Y. :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9(中譯本參杜維明,《論儒學的宗教性 對《中庸》的現代詮釋》,段德智譯,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白詩朗,“儒家宗教性研究的趨向”(彭國翔譯),《求是學刊》,2002年第6期(總第29卷),頁27-36;
方朝暉,《“中學”與“西學”——重新解讀現代中國學術史》,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任繼愈(主編),《儒教問題爭論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
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清代中期學術思想史研究》(第2版,北京:三聯書店,2005年版。
--------------------------------------------------------------------------------
[①] 但這決不是說本人輕視歷史學科的重要性。事實上,我傾向于認為歷史學科治思想史或文獻學的人(以及中文系古籍或文獻專業學者),在國學基礎方面往往比哲學學科培養出來的人強,這與他們較重視文獻資料的完整性與實證性有關。而哲學學科所注重的思辨性,恰恰與中國古代思想的特征傾向相距較遠,加上其對古代經典往往采取自取所需、隨意切割式閱讀,對古代學術傳統的歪曲最為嚴重,是導致今日國學凋零的主要原因之一。
[②] 有關儒學宗教性問題的爭論,參邢東田,“1978-2000中國的儒教研究:學術回顧與思考”,《學術界》(雙月刊),2003年第2期(總第99期),頁248-266;任繼愈(主編),《儒教問題爭論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方朝暉,《“中學”與“西學”——重新解讀現代中國學術史》,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參“儒學是宗教學說嗎?”章),等。國外研究狀況參白詩朗(John H. Berthrong),“儒家宗教性研究的趨向”(彭國翔譯),《求是學刊》,2002年第6期(總第29卷),頁27-36;杜維明,《論儒學的宗教性:對〈中庸〉的現代詮釋》,段德智譯,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杜維明,《儒家思想新論:創造性轉換的自我》,曹幼華、單丁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Rodney L. Taylor, The Religious Dimensions of Confucianism, Albany :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0。
[③] 參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清代中期學術思想史研究》(第2版,北京:三聯書店,2005年版)中有關章節。
[④] 參拙著,《“中學”與“西學”——重新解讀現代中國學術史》,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2年(參有關辯證法、及唐君毅和牟宗三研究部分)。
[⑤] 在這方面,我曾在近作《儒家修身九講》(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中專門作過較系統的分析。在該書中,我根據自己所搜集掌握的資料,對現當代的心理疾病和精神困境從多方面加以總結,并從儒家修身傳統中挑選出守靜、存養、自省、定性、治心、慎獨、主敬、謹言、致誠等九個范疇,來說明儒家修身思想對于診治現代人疲困的心靈所具有的強大現實意義。
[⑥] 參Wm. Theodore de Bary(1919-),Asian Values and Huamn Rights: A Confucian Communitarian Perspectiv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ombrideg, Massachusetts,London, Engliand, 1998(中譯本參《亞洲價值與人權:從儒學社群主義立論》,陳立勝譯,臺北縣:正中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版);狄百瑞,《中國的自由傳統》,李弘祺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3年版; Wm. Theodore de Bary &Tu Weiming(eds.), Confucianism and Human rights, 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杜維明,《論儒學的宗教性:對〈中庸〉的現代詮釋》,段德智譯,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Tu Weiming, “Implications of the Rise of ‘Confucian’ East Asia, ” In: Daedalus: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Winter 2000: “Multiple Modernities”, Vol. 129, No.1, pp.195-218; Tu Wei-ming(ed.),Confucian Traditions in East Asian Modernity: Moral Education and Economic Culture in Japan and the Four Mini-Dragons,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⑦] 《春秋公羊傳》對于無禮無義無道行為以夷狄稱之,有禮有義有道行為以中國稱之,無論當事人是中國還是蠻夷。例如昭公23年,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傳》曰:此為偏戰,而經以詐戰之辭言之,因“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又曰:“然則曷為不使中國主之?中國亦新夷狄也。”定公4年冬,經云“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莒,楚師敗績”。《傳》云,吳君之所以稱子,因楚伐蔡為無道,吳救蔡為有禮,是“夷狄也而憂中國”。
[⑧] 參拙文,“文明重建、中西學術與儒學的轉型——論當今儒學轉型的三個條件”,《哲學動態》2007年第5期,頁12-15;“走出學科的樊籬,回歸意義的重建——試談中國哲學今天面臨的主要問題與任務”,《哲學動態》2003年第10期,頁9-12。
[⑨] 有關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已經不少,參Asian Values and Huamn Rights; Shils, Edward, “Reflections on civil society and civility in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 tradition,” In: Tu Wei-ming(ed.), Confucian Traditions in East Asian Modernity: Moral Education and Economic Culture in Japan and the Four Mini-Dragons,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38-71; Peter K. Bol,“The Rise of Local History: History, Geography, and Culture in Southern Song and Yuan Wuzhou”,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1.1 (2001), pp. 37-76; Symposium: "Public Sphere"/"Civil Society" in China? Paradigmatic Issues in Chinese Studies, III, In: Modern China,Vol. 19, No. 2, Apr., 1993.余英時,《儒家倫理與商人精神》,南寧: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⑩] 在孟子有關“義”與告子等人的辯論中(《孟子·公孫丑上》),他更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踐仁行義是因為這樣做符合人性,是“由仁義行”,而不是“行仁義”(《孟子·離婁下》)。不僅在道德領域是如此,在其他領域也是如此。在與梁惠王有關仁政的討論中,孟子更是強調了仁政的成效之一在于可使人人“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孟子·梁惠王上》)。
[11] 狄百瑞觀點參Asian Values and Huamn Rights;杜維明觀點參Tu Wei-ming,Centrality and commonality : an essay on Confucian religiousness,A revised and enlarged edition of Centrality and commonality,an essay on Chung-yung, Albany, N.Y. :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9(中譯本參杜維明,《論儒學的宗教性 對《中庸》的現代詮釋》,段德智譯,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Tu Wei-ming(ed.), Confucian Traditions in East Asian Modernity: Moral Education and Economic Culture in Japan and the Four Mini-Dragons,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Tu Weiming, “Implications of the Rise of ‘Confucian’ East Asia”,In: Daedalu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Winter 2000: “Multiple Modernities,” Volume 129, No.1,pp.195-218;Tu, Weiming, Milan Hejtmanek & Alan Wachman (eds.), The Confucian World Observed: A Contemporary Discussion of Confucian Humanism in East Asia, Honolulu, Hawaii: Program for Cultural Studies, The East-West Center, 1994; 安樂哲等人觀點參Hall, David L. & Roger T. Ames, The Democracy of the Dead: Dewey, Confucius, and the Hope for the Democracy in China, Chicago and Lasalle, Illinois: Open Court, 1999.
[12] Asian Values and Human Rights, p.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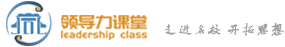




























 加多寶
加多寶 IBM
IBM 摩拜單車
摩拜單車 vivo\oppo
vivo\oppo 中興
中興 GOOGLE
GOOG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