蒂姆·布朗和艾德奧公司:最具創新力
總部設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艾德奧公司是一家被人們認為經理人很無趣、管理很差勁的公司,但這并沒有阻止這家公司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最具創新意識的公司之一。最近的一次統計表明,該公司的550多位設計師被《商業周刊》工業設計杰出獎提名的次數至少是它主要競爭對手的2倍,并且它在媒體“最具創新”的排行中也常常位居前列。
毫無疑問,艾德奧公司的領導人們知道自己公司的成功是因為公司管理的薄型化。當問起艾德奧公司的秘密,創始人大衛·凱利(David Kelley)曾說:“我只不過是雇了一些聰明人然后就全身而退了。”他說,他希望建立一家能夠“與朋友一起工作”的公司。
那么,如果不是“管理”將公司聚在一起,那是什么呢?一個詞,文化。公司的現任CEO,英國人蒂姆·布朗說:“我們事業的成功完全依賴于公司的文化來驅動。”什么樣的文化呢?布朗說,首先,像周圍其他的那些叛逆的領導者一樣,他并不是受過學習 的經理人,也談不上什么天賦,甚至是理想。他是學藝術出身的,曾想當一位畫家。他說:“管理只是協助人們做他想要做的事情的一種工具。”
“T型”當道
作為一家設計公司,艾德奧公司的工作以項目為基礎,類似于麥肯錫之類的咨詢公司。但是艾德奧公司又有很多自己獨特的性質。首先,“我們文化的關鍵一點是對新鮮的工作有持久不變的興趣”,而且同時對任何無新意的工作很排斥,不管這個項目能掙多少錢。布朗承認這對于這家需要成長和學習的公司是一個挑戰,但綜合起來他認為公司在整體上是好的。
第二個關鍵點是“我認為我們意外地找出了如何使背景完全不同的人能高度協作的方法”。能這樣做的其中的一個因素是非常細致的甄選流程。艾德奧公司招聘那些“T型”的人才,即不但擁有超群的技術而且還對身處的環境有極大興趣的人才。“I型”的人并不適用,但極少情況下也有這樣的人進入到公司,但最終會由于不適應艾德奧緊張、實驗性、高度協作的小團隊工作模式而離開,在這種環境下沒有人是被完全控制的,每個人都將對某一個設計方面作出貢獻。
艾德奧公司的第三個文化特征是它的創新模式是突發的而不是有計劃的。“沒有人會說我們今天要向哪個新領域進發,想法是憑空跳出來的。在一次合伙人會議上,我們試圖去勾勒出所有已知的公司正在發生的事情,不是客戶花錢讓我們做的那些事情,而是那些我們感興趣要做的事情。事實上,所有的這些項目都超出了我們在時間和空間上的限制。在某種層面上,這看起來像是很混亂,但我們看到這種突發的創新方式給公司帶來了很多不可思議的價值。”
原諒支撐艾德奧公司獨特創新文化的基礎是深度信任的匯集。這存在于公司的DNA中,部分起源于凱利希望與朋友一起工作的初衷,但同時也來自于他刻意地去創造一個積極鼓勵員工去接受創新冒險的組織,甚至即使是一項來自惱人客戶的任務,這在其他的地方是不被提倡的。“大衛經常談到要我們學會道歉,而不是尋求認可。 ”,布朗說,“放手去做事,如果到時候事情變得很糟糕,必要的時候就去道歉。但是在一開始來判斷這件事是好還是壞是否要去做則完全取決于你自己。”
這樣的文化能傳播開么?如果能,它能傳播多遠?比如在谷歌公司,文化是持續受到關注的。一方面,布朗承認從純效率的角度出發,艾德奧并不是很高效的公司。實驗精神意味著出現很多的混亂,對突發經驗的消化也需要消耗很多時間和大量的商務旅行。目前這還沒有對公司的成長造成影響,因為艾德奧發現一直在合作的大公司很多都不僅實力雄厚而且都有一些有趣的問題。同時,布朗聲稱已經在知識體系開發中取得了一些進展以對公司日益積累起來的經驗進行管理和利用。
下一站,世界
然而,有一個迫在眉睫的問題。布朗說,絕大多數的新員工對解決大企業的創新問題并不真正地感興趣。他們真正感興趣解決的創新問題是關于非洲農業、印度的凈水和健康甚至是北美的教育。“因此我們現在有這樣非常急迫的需求解決如何去調整我們的商業模式以迎合員工的興趣。我們今天85%的業務來自于西方的大企業。如果在5年后仍然要保持85%,我們要么企業規模是現在一半,要么我們就無法擁有現在的員工質量。因此,對我們的挑戰是,我們如何使商業模式與員工的激情融為一體?因為這是我們使公司成長的原始力量。”
有趣的是,布朗相信艾德奧公司毫無止境的創新思想需要打破新的創新邊界,但他認為結果將是很關鍵的。關于規模的真正問題,他說:“不是關于分享信息,而是關于分享靈感。如果我們能發現分享靈感的機制,我們就很可能成長壯大,而且我對我們現階段的發現感到很滿意。”
維尼特·納亞爾和HCL科技公司:爆發式成長
如果你是一家價值20億美元的服務型企業并為不斷增加的客戶需求而掙扎,你的供應商的技術正變得日益復雜,并且隨著業務的快速增長每年失去四分之一的員工,你該如何應對?你應該“摧毀CEO的辦公室”,并且告訴客戶你的員工是第一位的。
這就是印度IT和軟件開發公司HCL科技公司CEO維尼特·納亞爾在半月灣論壇上勾勒出的觀點。
HCL公司在2005年開始覺悟,當時的背景是:印度的軟件市場每年增長25%(出口值大概為400億美元)。 在一家擁有35 000名員工的企業中,為了保持每年40%的業務增長,每年將有8 000名員工離開。科技的復雜性像需求一樣如雨后春筍般地增長。納亞爾說,最近的一次數據表明,集成商需要熟悉862項技術才能做到以客戶為中心,“而且谷歌、惠普和微軟又時不時地制造出一些給你帶來更多問題和復雜性而且無法兼容的產品”。
打擊商品化
面對復雜化的癥結,HCL曾有過意外的發現。它意識到IT服務已經變成了商品化的市場,一個高科技的市場,但在供應商之間卻沒有真正的差異化。它們都說要以客戶為中心,“但是除了談論這件事,你還能從服務的觀點進行哪些創新呢?”
納亞爾考慮的結果是,可能他們完全搞錯了。這里不缺乏需要調整的客戶需求,也不缺乏需要調整的新問題。“但真正能給我們解決方案的人是我們的員工。對整個行業而言最珍貴的事情是,當員工遇到客戶時該做些什么?兩者互動的界面是價值被創造的地方。你的員工的素質越高,能力、效率、參與度越高,越能創造出更多的價值。”
如納亞爾所說,去扭轉這些的第一步是向童話故事學習。“我們大多花很多時間去胡說八道,告訴每個人我們的公司有多偉大。我們啟動了一個巨大的概念叫‘魔鏡啊,魔鏡’,而且我們確實把企業里隱藏的很多弊病帶到所有員工的面前,我見證了所有的這些。它釋放出了空前的能量,誠實確實是需要的。因此‘魔鏡啊,魔鏡’是我們常常需要提問的,它使我們保持誠實。”
這種邏輯就指向了組織的全面民主化,這是企業所畏懼的一種觀念,不像戈爾公司(Gore)或者全食超市(Whole Foods Market)已經在一種傳統的等級制度下運轉了接近30年。與其全面地調整企業的運營結構,HCL公司的解決方案是通過一系列創新來建立深度的文化變革。
逆向問責制
為了證明把員工放在第一位并不是說說而已,公司啟動了對所有經理人的360度評估,并把評估結果公布在網上。在過去的3年里,大概有2萬名員工參與了調查,為1500名包括納亞爾在內的經理人對20項與員工相關的績效進行評分。這個調查不與薪酬或晉升相關,但是它公開化的特性使得每個經理人不得不認真對待,努力去改善自己的缺點,或者在某些事情上改變方向,比如將領導職能更多地向以技術為導向轉變。
強調致力于不同種類的問責制,納亞爾的內部博客“維尼特答問”,允許員工對公司任何事物進行提問,所有的對話也將公布在公司的內部網絡中,所有的問題和答案都將不會受到抨擊。這就是重點所在。
納亞爾說:“我們對等級制度能帶給我們的確定性感到懷疑,我們想打破一個人說了算的狀況,因此我們啟動了被稱為‘毀滅CEO辦公室’的計劃。我們創造了一個等級并行的組織,包含了32個利益團體,人們能憑此展開協作并且創造等級外的機會,因此沒有人能對它進行控制。今天,經過3年后,HCL20%的收入來自于這些利益團體創造出的想法和倡議。”
所有人都能很輕松地說要做到員工第一,但是他們也曾聽到過這樣的疑問:你怎么能證明員工第一?HCL公司的答案很新穎:在行政部門和員工間簽訂服務水平協議(SLAs)。對任何的投訴或者咨詢,員工可以通過公司網站對需要進行回復的部門開啟一條服務通知,重要的是,只有員工才有權關閉這項通知。因為部門的服務質量取決于對服務通知的回復率和速度,因此就激勵各部門盡快地進行回復以關閉通知。納亞爾說,通過服務水平協議的方式去減少企業的官僚作風,發出了企業對創造價值的一線員工進行支持的信號。員工也成為更加積極的角色,他們鼓勵部門更具前瞻性,并且時間長了組織會真正做到以員工為核心。
杰弗里·霍南德和第七代公司:激勵反思
第七代公司沒有讓自己過得很輕松。它的產品都很基礎,比如廁紙、紙尿布和洗衣液,但它要求自己的產品不僅具有可持續性,還要有更多的附加價值,因此它并不在沃爾瑪進行銷售。該公司經營極度透明以至于它的代理律師每次公開發言時都不得不加倍小心。
總裁兼首席創意官杰弗里·霍南德說,“第七代”取自于《易羅奎法典》,意思是做任何事情時都應該考慮到對今后七代人的影響。“10年來我們雇用的任何廣告代理公司都勸告我們放棄這個名字,謝天謝地我們沒有。”
基本悖論
彼此相悖的是,第七代公司越不遵守傳統的商業模式,它經營得反倒越好。在20年前創立之后,這家私營企業連續經歷了虧損的12個年頭。作為一家私營企業,第七代不對外公開財務。然而,在20世紀90年代末,這家公司以每年25%的速度增長,去年增長速度達到了45%,今年可能更高。它是如何在這種悖論下做到增長的呢?
霍南德說,是因為透明化。表現第七代“精髓”的三要素之一是真實,這催生了對極度透明化的需要并成為一切的驅動(其他的兩個要素是正義和公平)。透明化指的是假如不好的事情發生不是要去掩蓋而是確保讓所有人都知道。這樣還不夠,比如說,公司試圖去除洗衣液產品中的一項化學元素,利益相關者必須參與到對話當中。“這樣做激勵我們檢查所做的任何事情,把所有大家可能關注的、可能忽視的問題都放在我們的網站上”,霍南德說:“你能夠如此的自我批判和透明化的想法是完全違反直覺的,但是我認為我們生活的世界中,人們都感覺到懷疑和不信任,但透明化也能起到相反的效果,這創造了一定的信任和安慰,是消費者很少能與消費品制造商建立的一種關系。”
反思與專注所有的這些都不容易。霍南德承認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第七代極端的自我反思和講真話的文化,“我告訴我的分析師只要我們還在這條路上,我將永遠不離開治療,因為我在一個時時刻刻進行批判和自我反思的地方,高層管理者很難不讓自己回到他們從其他企業里拿來的現成商業模式中。我常常開玩笑說我們正雇傭的人都被他們以前的公司破壞了”,他說:“你雇傭了一個人,你告訴他你希望他們誠實,你希望他們直接,他們不相信你;他們會說是啊,我之前聽過這些,我再也不會再上當了。成為別人信任的人往往要花費數年的時間。”
當他們能做到這一點,將會受益無窮:人們不僅對工作充滿激情,而且對公司鼓勵他們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感到興奮—“這是讓我最感到自豪和高興的事情之一”。“變成他們想要的”也是第七代公司試圖去告訴顧客的。霍南德承認持續的自我分析能使公司思想非常專注。公司非常努力地試圖看穿顧客眼中的決定,這些與傳統的客戶關注點不同。“我們認為我們與客戶建立的偉大關系是通過一種流程來幫助他們成為他們想要成為的人,并且幫助他們主導自己希望去主導的生活,我們認為很少有企業能通過如此這種抱負遠大的方式去真正了解他們的客戶,但這里確實存在著一個巨大的機會,尤其是在類似我們所處的這個行業。”
(本文首次發表于Labnotes 雜志總第十期)
評點:
學會“不務正業”
文/支維墉
這個命題甫一提出一定惹來嗤笑。我們中國人的思維定勢總是“在其位謀其職”、“恪盡職守”,如若不然就是“尸位素食”、“不孚眾望”。
其實,何謂“正業”,有時候真是很難定論。20年前的中國,最優秀的學生都去念電氣自動化;10年前,高中的精英們第一志愿常常是生命科學;如今,經濟管理類專業最為搶手。你看,就短短20年,一個剛剛開始規劃人生的少年根據社會風向為自己選定的“正業”就經過了數輪變遷。“正業”的邊界之變化,正應了王菲那句歌詞:“沒有什么會永垂不朽。”
魏晉以降,文人們或宦海沉浮、經世治國,或歸隱田園、梅妻鶴子,都算是一種正業,前者居廟堂之高,后者處江湖之遠,但都或明或暗地向往著、覬覦著政治和天下。仿佛只有“先天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才叫務正業。不過偏偏有個徐霞客,一人獨涉山水數十載,不為官場職稱,亦不為暴得文名,終成不朽的《徐霞客游記》。還有個徐光啟,不僅做官,還在閑暇之余翻譯《幾何原本》,編撰《農政全書》,順便向內地引進紅薯。這在當時可算得上是不務正業了,但數百年之后,當搖搖欲墜的清帝國開始發現自然科學是當務之急的“正業”,徐光啟就成為了中國西學東漸的肇始之人。
“業”之“正”與“不正”不必拘泥于眾人所想,如徐光啟之言:“名理之儒士,苴天下之實事。”
回到管理世界。文中提到三位CEO因為在組織設計和企業文化等方面投注過多精力而可能被視為 “不務正業”。事實上,這更像是中國人的眼光。中國的企業家們,總是把創新、領導力、組織變革等視為不務正業。正如博斯公司的謝祖墀總結說:“中國企業在過去30年追求的都是規模、產量、低成本、財務實力、功能性品牌和技術優越性這些硬實力指標,而在發展領導能力、創新型的管理風格以及塑造技術生態系統等軟實力建設上做得不夠。”
有了這樣的先決態度,很多事情也許真的變得越來越不務正業。六西格瑪、平衡記分卡等管理工具,大都在中國的企業遭到慘敗,草草收場。咨詢公司的報告,也多是為了佐證決策者的決定而精心炮制。
當然也不須過分悲觀。中國最優秀的企業現在也開始學著不那么務正業。“賺錢”應該是企業最大的正業,但馬云最近卻給淘寶和支付寶定了一個“收入上限指標”,不準它們的收入超過某個數字,否則高管就要被懲罰。此舉旨在抑制這兩家公司收入過快增長,因為馬云認為現在還不到賺錢的時候,有了錢就要投入市場,把蛋糕繼續做大。不寧唯是,阿里巴巴現在似乎更關注其企業文化能否有效傳承。阿里巴巴集團一位副總裁說,現在他們最擔心的,就是因為企業規模擴張過快而導致其企業文化被迅速稀釋。因為“500個老人去影響2000個新人是一件很難的事情”。為此,阿里巴巴很愛召開全務虛的會議,大談戰略和文化,據說很多人在會上情緒投入以至于“痛哭流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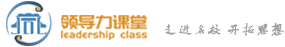








 加多寶
加多寶 IBM
IBM 摩拜單車
摩拜單車 vivo\oppo
vivo\oppo 中興
中興 GOOGLE
GOOG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