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你見過華為文化中的殘忍一面乎?一個年入老齡的銀發人,不論你曾經擁有過何等輝煌的經歷、資歷、學識,來了就“清零”,一律要進“新兵營”。也幸虧朱士堯教授對此感到“新鮮”,能“自虐”,咬牙堅持。教官對他雖“手下留情”,但入職集訓下來,他告訴我:“沒想到,我體重居然減了不少斤”。他入職華為集團黨委,很快被增選為黨委副書記。哈哈,“廉頗老矣”也有現代版,他以近乎凍齡的面貌,“空降”華為。
因與教授的歷史淵源,我在讀書節前一周,即這本《華為的精神原子彈》上機印刷之時,就拿到了全書PDF版,先睹為快。這是一本精裝,造型炫酷的新書,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出版社,不難想到,那是出高端理科教科書和發表科學文獻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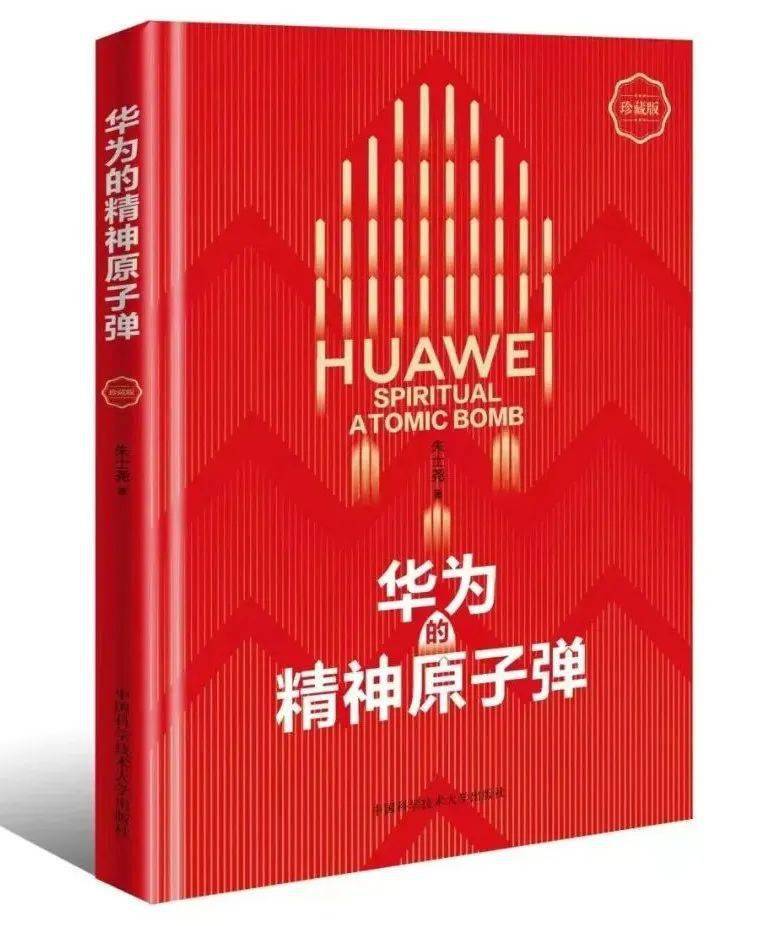
《華為的精神原子彈》
朱士堯/著
當紅色的、微小的電子書影,以焦點模式從手機上秒彈,瞬時霸滿屏幕的時候,她是那么吸睛奪目,打動了我。幾秒之內,就毫無懸念,抓走了我的注意力,喚起聯想,引出長江水般的滔滔思維。
一字不拉讀了這本新書。暢快的信息流,如電流般擊穿了“我這小心臟”,打開了一個腦洞,也讓我“惡補”了一把什么是華為。那感覺,爽,就像一個老牌“黔之驢”,到位“美酒河”,痛飲了極品茅臺。
算下來,作為一個上一世紀九十年代進入深圳的移民,我與華為,在同一個城市,工作、生活,也有三十余載。業別不同,卻也近距離旁觀華為的發育、成長,一波三折。華為是我一進入深圳,就企圖深入了解的對象。然而,作為一個職業記者,我的這份“陰謀”一直都沒有得逞;而作為華為老板的一個小“老鄉”,我曾與任正非一樣也走進過大山,見過地區經濟與民眾的生活貧困。雖有機會參與廣東貴州商會的不少活動,然而遺憾的是,在這些活動的若干場合,我們迎來過思想家朱厚澤、博鰲論壇原秘書長龍永圖和一些著名經濟學家,卻始終沒見到任正非。按那些老鄉的理解,無論是怎樣成功或失敗,他都是最有資格成為貴州青年創業企業家的“教父”的任正非低調,任人評說,專心華為,心無旁騖。可越低調,卻越激發人們想了解他、了解華為的渴望。
可是,很長一段時間,我對任正非與華為的了解,也只是報紙、網上、口碑里聽聞一些碎片:“床墊文化”、“狼文化”;坊間傳華為企業資產負債率極高,到底多高?卻也一直沒見到精確的數字化權威描述。不知能與當下貴州省68%的外債率相比么?
與許多行業企業相比,華為員工的收入可觀,考核自然很嚴。我認識的一個華為采購經理,就為考核年年優秀到不能再優秀了,自認遇到天花板,選擇提前退休。有人評論,這完全不是體制內人的風格。
還有一年(90年代),我參加深圳市稅務局舉行的一個表彰會報道,見證了華為成為時年超50億元人民幣的深企納稅大戶而被表彰,孫亞芳出席發言領獎。那年月,我們還在蘭光大廈上班,跑線記者收到幾份《華為報》,我在本報編輯部就讀到了任正非那篇著名的奇文《華為的冬天》。可以說,這是我讀過的中國企業家,認知最清醒的文字;還有一次,我到北京出差,見到首都新聞界對當時華為員工高學歷化——博士碩士罕見地達到7000人(現在應更多)的議論與爭論。華為成了一個高學歷收割機。信息不對稱,人們看不懂華為,卻又對華為如雷貫耳。
對我而言,華為是一個謎。這個謎,終于在朱士堯教授到來深圳,有了一點鉆墻透氣的感覺。
1
一位理工男的“銀發”遠征
其實,說華為信息全無,悶聲發財,未必是公道的。不說自媒體、網絡中,各類寫華為說華為的汗牛充棟,機場售書亭,熱賣華為書,常讓人目不暇接。但他們可信么?說華為一多,反而感覺華為被一層信息繭包裹,讓人搞不清繭內生命體的面貌,把不到它的脈搏,聽不見它的心跳。
朱士堯教授的到來,讓我獲得了一個意外驚喜。2005年3月,他年滿60,退休一周,開啟61。一頭烏黑頭發,單身一個,從一個城市帶區域經濟邊緣,安徽合肥,一步跨進了華為總部。你見過華為文化中的殘忍一面乎?一個年入老齡的銀發人,不論你曾經擁有過何等輝煌的經歷、資歷、學識,來了就“清零”,一律要進“新兵營”。也幸虧朱士堯教授對此感到“新鮮”,能“自虐”,咬牙堅持。教官對他雖“手下留情”,但入職集訓下來,他告訴我:“沒想到,我體重居然減了不少斤”。他入職華為集團黨委,很快被增選為黨委副書記。哈哈,“廉頗老矣”也有現代版,他以近乎凍齡的面貌,“空降”華為。
如此說來,朱士堯教授何許人也?
2005年,我在深圳上梅林第一次見他,請他喝茶,他掏出的名片,還是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教授、研究生院副院長老名片。聊聊才知道,科大研究生院院長是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當時兼任中科大校長的嚴濟慈兼任。朱這樣的小字輩副院長在合肥主持研究生院日常工作。一向對科大情有獨鐘的華為,聞朱退休,逢華為集團黨委面臨換屆,不拘一格的華為,巧借天力,把朱士堯教授聘到深圳。
老天給出時空縫隙,賦予朱士堯教授一個新的詩和遠方,獲得人生中的華為十年。自此,我與朱士堯教授同城為伴。說起來,我們的淵源,可以推到1982年,在貴陽市龔家寨,我們有一次沒見到面的“相遇”。朱士堯教授1968年畢業于中國科技大學原子核物理系。在史無前例的“探索”中,他十分有幸,早在1973年(十年浩劫遠未結束)就被母校選調回中科大當一名大學教師。說明他是個學校難舍的高材生。在他返校當大學老師時,與他同時代的大學畢業生絕大部分都還在廣闊的農村種地、喂豬。
中國科大是中國科學院所屬、專門從事前沿科學與高新技術研究與人才培養的大學。首任校長郭沫若。1969年12月至1970年10月,科大由北京搬遷到合肥。網載:科大搬遷,為一塊落腳之地,曽找過河南、湖北、江西、安徽四省,只有李德生主政的安徽,把科大接納進了合肥。據說,科大搬遷,用了70多列貨運列車,裝載了35000箱儀器、圖書,在車廂上貼了“軍用物資”的標簽。可見這與抗戰時的那場西遷有一點類似。
家父曾調侃:“朱士堯教授是個書呆子”(意朱勤奮善學,人才難得)。1978年,科學春天到來,科大重入正軌。1983年,朱士堯教授被國家選拔,送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當訪問學者。1985年,我受中國青年報學校教育部調遣,赴山東、安徽、江蘇搞職業教育調查,到過合肥。周末我去了中國科大。那時朱士堯教授人已遠赴美國,我千里迢迢到他家,又沒見到他。朱夫人嚴老師領著我參觀了一圈科大。教學樓、圖書館、實驗樓,轉到宿舍區,她指著一幢紅磚樓,告訴我第幾單元幾樓住著溫元凱一家。溫那時正因超前的改革演講,躥紅為時代明星。他恢復高校招生的建議,被鄧小平采納。
我第一次見到朱士堯教授的著作應該是1992年。龔家寨家中收到他寄來的一本研究生教材《核聚變原理》。手捧這本裝幀簡陋、散發著油墨味的新書,我的手發燙出汗。我的大學,骨干課程是《古代漢語》、《古代文學》、《現代文學》等等,晨煉誦讀,不是背英語單詞,就是先秦散文、唐詩宋詞。即便是復課鬧革命時期讀的中學,我們那屆中學生沒開過物理課。朱士堯教授的書,對我而言,簡直是一本天書。我和它隔著的不僅僅是一座座大山,還根本就天南地北。
蹉跎歲月、歲月蹉跎,短缺時代轉型期,偶遇一本書,能學進去,往往就能造就一個人。可我這樣的一個人,這時遇到這樣的書,意味著什么?如今三四十年過去了,能玩味這指頭縫里流走東西,也生發許多遺憾的感覺。我家至今還保存著朱士堯教授的這本書,書已泛黃變色成了舊書,但卻頗有“為了忘卻的紀念”意味。
自然科學里,物理學是一門居于基礎與充滿活力的帶頭學科。60前,朱士堯教授是個行走在科學領域的中科大人;61后是個幾乎把骨髓都融入華為的華為人。他長期在中國科大這樣的高等學府里孜孜不倦,培養出了扎實領悟科學知識的優良素質,這使他在華為很快能找準事業方向與人生定位。
我編輯《經濟瞭望》時,曾編發過朱厚澤的一篇奇文:《無限的智能與智能的無限》1。那時全球背景,知識經濟如日中天,中國改革開放的時空坐標,也在迎接這一新經濟浪潮的挑戰。改革還在路上,開放能帶動一切嗎?思想家朱厚澤這篇近乎于科學哲學的美文,達到了“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的境界。他高屋建瓴,見識卓越,觀察到了時代搏擊的浪花四濺,剖析了前沿智能與智能經濟,科學發現與創造創新之美,流露出對走向未來發展博弈的深刻思索。
原本就在一個最能接近“無限”的基礎學科領域和學府,朱士堯教授又有緣轉身來到華為,這使他的“轉型”換角色,再度深耕,有很豐厚的專業積累打底。這門專業基礎,竟使他像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出訪花旗國的林鍼(zhen)一樣,學到并懷揣上了一種絕技——“神鏡法”(照相術)2,能手持從沒見過的“獨門機器”對準華為。
三年新冠疫情,一個無奈的“靜”字,成為難忘的記憶。不能例外的靜默中,朱士堯教授卻能調整狀態,“深諳核科學的原理和規律,深知核威力之大”(孟凡馳序),于是聯想使他超級發揮比喻的功能,跨界拍攝與顯影華為。
2
朱士堯教授呈現了華為的什么
如果說,朱士堯教授的新著《華為的精神原子彈》(以下簡為《原子彈》),那他開張需要給大家科普的是原子彈原理。《原子彈》只一用了一章,兩小節,就說清了理解華為文化所需要的和物理基礎知識。二小節,“從愛因斯坦說起”,“曼哈頓計劃”,僅用了全書約二十分之一的文字分量,就干凈利落,設定了審美觀照華為精神文化的文本底片。為解讀華為,給出了一個獨特視野。
用原子彈的威力襯托華為文化,可見這文化的非同尋常。
那文化是什么?一個企業,誠如華為,它新生、崛起、壯大、追求可持續,為什么會這樣去建構如此一個“超級能量”的企業文化?
原文化部部長孫家正曾定義“文化是一個民族的靈魂”(2007年),一時被廣泛引用。如斯類推:華為的企業精神文化,是華為作為一個企業,賴以產生生命力、凝聚力與創造力的靈魂。它對內對外,都可以修持塑心塑人,產生軟實力才具有的那種征服力。
有專家高論:歷史科學中,文化與文明是兩個不同的詞,但含義相通。往往在歷史過程中,能運動或運動著(如傳承)的就是文化,能積累沉淀結晶的就是文明,如四川廣漢三星堆文化與三星堆文明。文明凝聚凝結著文化,在時空長河里,文化是發育與流動的,文明則是人文積累可以物理具象化的又一種呈現。文化與文明都是人類學歷史學很大的概念。
為研究便利,社會學設定了一個族群概念,用以區分不同的文化族群。
但今天的華為,是一個跨國跨族的人類聚合體。走在國際化路上的華為人,如今已不簡單是某單一民族、國別。他們在數量上集合為一個集團,共生點是企業、產業,當然出發地是中國深圳。從創業6股東,到擁有二十萬多國科學家、工程師,華為組成一個征戰商海,發展企業的群體。如此一個數量上不算少的人群,集合搞企業謀發展,當然離不開經營內外兩種“文化生態”。而這種“生態”必然生成企業文化。
朱士堯教授之才具,在這本新書中,表現出兩大優勢:一是原有知識背景,二是零距離置身于華為的心臟,直接參與經營華為文化生態,從事華為文化建設實踐,可以說是無障礙地觀察體驗、系統梳理、總結華為文化。兩大常人不具備的優勢,使朱士堯教授的“照相術”具有超級景深和文化廣角,而他一流的歸納演繹能力,使新書的“跨界鏡像”呈現為一個系統工程。在一個“微觀世界”里,進行全景式的“宏大敘事”。據我所知,如此系統地展示華為文化,還是第一次。
本書的形成,伴隨著一個朱士堯教授在國外國內不斷演講,已不下1200場。他的震撼演講,我至少見證過三場。講者精神矍鑠,全程站立,口若懸河,妙語迭出,聽者振奮。我在香港《經濟導報》工作期間,還作過一次朱士堯教授的大型專訪,編發了一期封面專題文章。從發行角度,那時我們的雜志,是進入中南海的。
演講的背后是不斷的思考與梳理、歸納與提煉、不斷完善,時有新的創見。朱士堯教授這本華為文化,內容內涵都是極為豐富的,本文限于筆者的理解角度,覺得他描述的華為文化有三個搶眼點:
第一,“智庫”參與與危機意識
其實中國人民大學的幾位學者田濤、吳春波等,組成團隊進入華為提供咨詢,時間遠遠在2012年《下一個倒下的會不會是華為:任正非的企業管理哲學與華為的興衰邏輯》(以下簡稱《下一個》)一書出版之前。
早于這本《原子彈》新書面世之前,朱士堯教授就告訴我,田濤、吳春波著的《下一個》,值得一讀。華為總部還在南山科技園時,他們就被任正非請進了華為。他們對華為進行了長期跟蹤服務,他們提供的研究,反應、見證與集成了任正非管理企業的哲學思想,也詮釋、演繹、呈現了這一思想。即使是在順風順水時,任正非也是一個永久牌的危機意識持有者。有人說“一部華為的發展史,就是一部危機管理史”,說明華為管理者立身的高度,修為的理性。這種哲學姿態決定了華為意識,具有鮮明的“自我批判性”。什么叫覺悟?自省?我想就是認識危機。批判成就了偉大,激發超前危機管理。危機意識成了華為知不足,學不止,大力度投入研發的理性邏輯。
某種意義上,朱士堯教授的《原子彈》與《下一個》構成了姊妹篇。朱士堯教授新書,以及田濤、吳春波等,與任正非的互動,揭示了任正非的集思廣益,人設寬廣,身邊云集科學家、工程師、“智囊團”。華為文化,因之疊加了當代“智庫”的機制,吸收有“智庫人”的積極作為。這正是高科技企業發展,創造企業文化過程中專業主義的一種存在。
我為配合單位和綜合開發研究院并肩,做深圳的“全球腦庫論壇”(腦庫后改為智庫),2004年,曾與研究院專家一起到訪過蘭德公司。那次難忘的“智庫行”,使我們觀察到任何一個對的決策,不僅需要決策者的智慧,也離不開智庫的相輔相成。如此,才能減錯、糾錯,不犯錯誤的人是沒有的。
第二,開放學習中有一個真“舍得”
即便是華為今天遭遇華盛頓的制裁,我們注意到任正非的言論、態度,也并沒有否認、羞辱、妖魔化自己的老師。他在頑強抗壓、直面危機中,努力自強,卻也不動搖、放棄開放的發展理念,不違投身改革開放的深刻初衷。
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華為。賣交換機的小公司華為,如今已是在全球170多個國家和地區開展業務,有近三分之一員工是外國科學家、工程師的跨國企業。
多次聽朱士堯教授演講,也有機會和他私聊,不時聽他講到華為拜師學藝,還有高水平的美國老師。但每一次都是話到即止,都沒有明打明說這美國老師是國際著名的麥肯錫,還是哪家頂尖大學、研究機構。難道給華為咨詢是一個簽約保密項目?這一度成了我的一個疑問、一個糾結。華為在美國,究竟請了一個什么樣的大牛老師?怎么請到的?花了多少學費?網上有文字猜測,但說的是模糊“天價”不會低于5億美金。
《原子彈》這一次不加任何渲染和形容詞,透露了一個“獨家猛料”。華為的大牛老師是美國頂級的IT企業IBM。根據研判,當時華為面臨與IBM曾遇到過的棘手問題一樣或相似,故華為決定一眾高管“西天取經”,飛越太平洋,來到IBM學習、研修,并簽約長期請顧問,一定要大幅提升華為管理現代化的水平。要學就學世界頂級的,但要老師拿出真經真心傳幫帶,就必須付出足夠學費。付多少?人家提一口價:20億美金。20億美金是多少?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終于走出最初創業時的囧境,成為國家級的重點智庫,每年收益達一個多億人民幣。也就是說,這20億美金,相當于該研究院干30—40年。華為不少高管心里嘀咕,老板不會答應這個價格。沒想到任正非一口答應。君子一言,駟馬難追。能教——“傳幫帶”華為成為世界級公司,這個“管理科學軟件”,該是個多大價值?2000多年前,孔夫子周游列國,收一個學生,還需要一束肉干呢!有人考證說,這一束肉干為10片,每片為半只羊,一束相當5只。弟子3000,肉干相當羊1.5萬頭。按現價200元一頭,這個戰國時期“國際”《論語》班收費,相當一個學期300萬(有點夸張哈,參見百度)。
經濟學家樊綱研究發展經濟學,說發展中國家有一個“后發優勢”,你在“信息對稱”領域下功夫,往往能縮短后發國家的趕超時間。回到華為彼時彼地場景,假定老師(道路自信)真能讓你達到這個對稱,你又有什么舍不得?
這是只讀了一遍《原子彈》,憑記憶,重新呈現書中的一個華為的故事。復述得不知準不準?好在新書很快面世,有心讀者可以去從容閱讀。新聞有時是被深埋藏在歷史文本中的。這使我們在深讀歷史文本和見識文物時,竟有一種重新發現“新聞事實”的感覺。這種發現是對靈魂的救贖么?我有一位同事,出于對歷史中的新聞的求知欲,重金買了一套鐘書河編的《走向世界叢書》2,結果發現在300年中,出洋的中國人都看到了什么樣的世界,學習了什么,這些看到并被帶回來的東西,又是怎樣影響和改變、甚至顛覆了沉浸在中世紀的故國。中國需要現代化,可以說是在看世界中看出來的。開放有可能帶動一切。20億美元學費付給了IBM任正非不心痛嗎?他沒路找路時,吃飯也不是沒問題啊。華為文化,也是花20億美金(多少人睡床墊)砸出來的,這是否有點令人唏噓?
第三,“糨糊”里一味藥的巨大粘性
《原子彈》一書中抄錄了一段任正非談自己、實際也是妙論華為文化的“論語”:“我只是提了一桶糨糊,把十八萬人粘起來一起奮斗”(任接受德國電視臺采訪談話)。在筆者看來,朱士堯教授這次“抄”作業,恰恰表明他的“神鏡法”,抓到了華為追求基業長青的“魂”。這個魂就是這個“粘”字。
以科學理性的思維,可以把華為文化看作是一個已有模樣,但仍在建設、仍需經風雨的一座大廈。那如此這文化的本質,也是一種“工具理性”意義上的屠龍術。仔細琢磨這桶“糨糊”,你會覺得,它是華為的一把開山斧、鋪路機。
極致的企業管理,不在于老板一個人能做什么,其文化的靈魂是能粘住所有人一起做,從而形成各盡所能的局面,日臻達到集成整體創造力的至高境界。由于筆者對華為的孤陋寡聞,因此也特別注意到,朱士堯教授的《原子彈》中,清晰地用了一段文字,平鋪直敘了華為工會的作為。華為工會承擔了華為實踐“工者有其股”中的這個“有”字操作,為全員操持股權管理。啥叫全員持股?全員持股是普通員工分享要素分配的具體路徑。它的含義是“華為這個大廈的磚瓦,有一塊是我的”,這是營造華為生態的一個根本,由此也生發著讓華為文化的精髓。啥叫“不叫雷鋒吃虧”?就是給愿意無條件奉獻的人,以應有的權益,而不是用美名實施了實際上的剝奪。這其實是中國式反極左的另一層含義,是一種提倡奉獻和實行公平的有機平衡。實際上是找到一條具體機制,解決長期困擾工會工作,究竟是重點突出“整體利益”還是“具體利益”的問題。因為“具體利益”變成了看得見、摸得到、拿得走時,就相當于給做大“整體利益”,安裝了一臺發動機。
此前,我真不知道在華為替老板提桶、刷糨糊的機構是華為工會。讀大學前,我曾有一段在國企當工人的經歷,見過“工會是干什么的”。印象中基本是:搞點文體活動,發發勞保品、女工保護用品,處理工傷事故后事。后來又多了一件:控制計劃生育指標。但時代使華為工會,成了一個“員工資產管理中心”,踏實幫助員工實現經濟權益上的那個“我”。
“此間不可無我音”。在全員持股的制度設計里,“華為工會代表華為全體員工持股99.2%;任正非持股僅有0.8%。2019年,華為曾邀請部分媒體記者,參觀了華為工會員工持股資料”。這有點像讓大家看到了一份按勞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結合的一個財務過程,操作工序,讓人們看到了這件事,含有一個遠遠超越經濟學意義的文化亮點。
華為因這劑猛藥,使華為粘成了真實的命運共同體。
華為的起點就是股份公司,華為員工持股,源于DNA級深層清晰的產權制度設計。如此傳動出來的企業文化凝聚力的深層結構,也洋溢著動力澎湃的活性。企業改革,就是搞活企業。所謂企業活力四射,實際是動力結構和企業文化的深刻互動,而這個過程在華為是由工會管理的。工資、獎金、股權,考評、奉獻、工資和獎金如何切換增減股權,這些實現了員工與企業效益掛鉤的“金飯碗”。金碗當然會產生文化魔力,華為員工持股,也就活生生變成了一副“金手銬”。
改革走到今天,股權人人在玩,但像華為這種玩法和文化效應都是罕見的。華為一路奮斗,“床墊文化”實際是“玩命地干”、“拼命地學”、踏實做事、高效率做事,企業文化構成了一種征服人心的魅力,這魅力是會產生心理效應的。這效應體現了華為文化里的糨糊之粘,紐帶之力之偉,對外沖擊力之威(并非沒有親和力)。
華為工會承擔起的角色,發揮出的作用,在我看來,這就是微觀企業工會的體制改革與機制創新。它體現了華為在改革開放中,內在機理的“變”。它充分顯示了華為文化的建構性,頗有一些阿馬蒂亞·森《以自由看待發展》3,樊綱《新經濟與舊體制》4對于新建構的探索之韻。
我在做與中國改革密切相關的歷史回顧時發現:我國第一代踐行經濟體制改革的經濟學家,如馬洪、蔣一葦、林凌,在從事經濟研究前,都有從事企業工會工作的經歷,他們在1984年代研究建構經濟體制改革時,都深刻考慮過工會改革問題;他們認清了企業改革,只有從國企“擴大自主權”,推行承包制,到實現企業股份制。他們都參與了深圳改革乃至企業改革的制度設計和咨詢。他們都從對國情的體驗出發,深刻認識到企業改革,無可回避的一個問題是:國家積累與個人利益怎么切蛋糕,怎樣做,做到什么程度才能實現雙贏,達到尊重個人,釋放活力的效果。他們不斷探索、研究、參與追蹤跟進改革進程,摸的就是如何合理擴大個人收益比例與國家利益雙贏的那個“黃金切割線”。
華為的出現本身就是這場改革開放大樹上結出的一個金蘋果。這使華為在DNA層面,出生就不是一個國企。走到今天,華為的意義不簡單實踐、找到了路徑、讓宏微觀結合互動,還在于發育生成了朱士堯教授筆下威力巨大的華為文化,這種文化的量級堪比原子彈,其結構相當于新一代航母換裝了核動力。
華為建設未來,創造力、生存能力,起點和過程,都時時在強化危機意識,處處都在思考客戶第一,給自己一個永遠的奮斗者定位。華為文化就是要讓企業也就是讓華為每一個人置身于“永動機”與不懈怠的文化心理與文化狀態的場景里,內外結合建設企業生態、文化生態。有這樣文化的企業會不會基業長青?在復雜的存在大量不確定風險的世界里,怎樣做才能更好地生存發展?
華為在迎接挑戰,相信歷史會給出回答。在這樣的意義上,朱士堯教授“跨界鏡像”之作,也就有了他的獨特價值和特定意義。
不管我的描述對不對,評論是否準確,但我都有足夠的理由,為朱士堯教授的人生喝彩。
—— 2023年5月9日于貴陽
參考文獻:
1.《朱厚澤文存(1949--2010)》朱厚澤著;世界知識出版社2014年3月第一版,見第283頁。
2.《走向世界叢書》鐘書河編;岳麓書社出版 第一卷 見第20頁。林鍼:1847年,中國第一個出洋的知識分子,著有《西海記游草》。“神鏡法”指林在美國學習的照相術。見鐘書河序《從坐井觀天到以蠡測海》。
3.《以自由看待發展》阿馬蒂亞·森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2年7月第一版。
4.《新經濟與舊體制》樊綱著;中國經濟出版社 2018年7月第一版。

























 vivo\oppo
vivo\oppo 夏普
夏普 樂視
樂視 富士康
富士康 奇虎360
奇虎360 亞馬遜
亞馬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