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當時的北平有十幾所大學,還有若干所專科學校。學校既多,難免良莠不齊。有的大學,我只聞其名,卻沒有看到過,因為,它只有幾間辦公室,沒有教授,也沒有學生,有人只要繳足了四年的學費,就發給畢業證書。等而上之,大學又有三六九等。有的有校舍,有教授,有學生,但教授和學生水平都不高,馬馬虎虎,湊上四年,拿一張文憑,一走了事。在鄉下人眼中,他們的地位就等于舉人或進士了。列在大學榜首的當然是北大和清華。燕大也不錯,但那是一所貴族學校,收費高,享受豐,一般老百姓學生是不敢輕叩其門的。
當時到北平來趕考的學子,不限于山東,幾乎全國各省都有,連僻遠的云南和貴州也不例外。總起來大概有六七千或者八九千人。那些大學都分頭招生,有意把考試日期分開,不讓學子們顧此失彼。有的大學,比如朝陽大學,一個暑假就招生四五次。這主要是出于經濟考慮。報名費每人大洋三元,這在當時是個不菲的數目,等于一個人半個月的生活費。每年暑假,朝陽大學總是一馬當先,先天下之招而招。第一次錄取極嚴,只有極少數人能及格。以后在眾多大學考試的空隙中再招考幾次。最后則在所有的大學都考完后,后天下之招而招,幾乎是一網打盡了。前面者是為了報名費,后者則是為了學費了。
北大和清華當然是只考一次的。我敢說,全國到北平的學子沒有不報考這兩個大學的。即使自知庸陋,也無不想僥幸一試。這是“一登龍門,身價十倍”的事,誰愿意放過呢?但是,兩校錄取的人數究竟是有限的。在大約五六千或更多的報名的學子中,清華錄取了約兩百人,北大不及其半,百分比之低,真堪驚人,比現在要困難多了。我曾多次談到過,我幼無大志,當年小學畢業后,對大名鼎鼎的一中我連報名的勇氣都沒有,只是湊合著進了“破正誼”。現在大概是高中三年的六連冠,我的勇氣大起來了,我到了北平,只報考了北大和清華。偏偏兩個學校都取了我。經過了一番考慮,為了想留洋鍍金,我把寶壓到了清華上。于是我進了清華園。
同北大不一樣,清華報考時不必填寫哪一個系。錄取后任你選擇。覺得不妥,還可以再選。我選的是西洋文學系。到了畢業時,我的畢業證書上卻寫的是外國語言文學系,不知道是什么時候改的。西洋文學系有一個詳盡的四年課程表,從古典文學一直到現當代文學,應有盡有。我記得,課程有“古典文學”、“中世紀文學”、“文藝復興時期文學”、“英國浪漫詩人”、“現當代長篇小說”、“英國散文”、“文學批評史”、“世界通史”、“歐洲文學史”、“中西詩之比較”、“西方哲學史”等等,都是每個學生必修的。還有“莎士比亞”,也是每個學生都必修的。講課基本上都用英文。“第一年英文”、“第一年國文”、“邏輯”,好像是所有的文科學生都必須選的。“文學概論”、“文藝心理學”,好像是選修課,我都選修過。當時旁聽之風甚盛,授課教師大多不以為忤,聽之任之。選修課和旁聽課帶給我很大的好處,比如朱光潛先生的“文藝心理學”和陳寅恪先生的“佛經翻譯文學”,就影響了我的一生。但也有碰釘子的時候。當時冰心女士蜚聲文壇,名震神州。清華請她來教一門什么課。學生中追星族也大有人在,我也是其中之一。我們都到三院去旁聽,屋子里面座無虛席,走廊上也站滿了人。冰心先生當時不過三十二三歲,頭上梳著一個信基督教的婦女王瑪麗張瑪麗之流常梳的纂,盤在后腦勺上,滿面冰霜,不露一絲笑意,一登上講臺,便發出獅子吼:“凡不選本課的學生,統統出去!”我們相視一笑,伸伸舌頭,立即棄甲曳兵而逃。后來到了五十年代,我同她熟了,笑問她此事,她笑著說:“早已忘記了。”我還旁聽過朱自清、俞平伯等先生的課,只是淺嘗輒止,沒有聽完一個學期過。
西洋文學系還有一個奇怪的規定。上面列的必修課是每一個學生都必須讀的;但偏又別出心裁,把全系分為三個專業方向:英文、德文、法文。每一個學生必有一個專業方向,叫Specialized的什么什么。我選的是德文,就叫做Specialized inGerman,要求是從“第一年德文”經過第二年、第三年一直讀到“第四年德文”。英法皆然。我說它奇怪,因為每一個學生英文都能達到四會或五會的水平,而德文和法文則是從字母學起,與英文水平相距懸殊。這一樁怪事,當時誰也不去追問,追問也沒有用,只好你怎樣規定我就怎樣執行,如此而已。
清華還有一個怪現象,也許是一個好現象,為其它大學所無,這就是“每一個學生都必須選修第一年體育,不及格不能畢業。每一個體育項目,比如百米、二百米、一千米、跳高、跳遠、游泳等等,都有具體標準,達不到標準,就算不及格。幸而標準都不高,達到并不困難,所以還沒有聽說因體育不及格而不能畢業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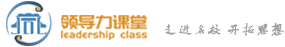












 IBM
IBM 加多寶
加多寶 騰訊
騰訊 vivo\oppo
vivo\oppo 娃哈哈
娃哈哈 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




